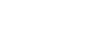標題:碧薩先生
「粗菜館」的貴哥晚上十點多鐘打電話給我:「有個導演,名字沒聽清楚,說是你的朋友,要找你。」我請他本人來聽,原來是已經十幾年沒見面的桂治洪。
七十年代中桂治洪在邵氏拍過許多好電影,《成記茶樓》、《血證》、《鬼眼》、《萬人斬》等等。還有幾部在馬來西亞導演的馬來片,迄今還是賣座最高紀錄保持者。
飛車趕到,桂治洪和攝影師小李及李太在等我,桌上沒有菜餚。「怎麼不叫點東西吃吃?」我問。
「吃飽了才來,主要找你聊聊。」桂導演說。他沒有變多少,頭髮有一撮白了,身材還是像以前一樣,略胖。
「這些年來,幹甚麼?」
「賣碧薩,意大利薄餅。」
「在哪裏?」
「洛杉磯。」
「市內?台灣人麕集的蒙特奧花園?」
「不,」他搖頭:「在一個墨西哥人區,說了你也不知道。」
「大導演怎麼會去賣碧薩?」
「人總要活下去的呀。」他說:「我不像阿孫,他到了美國還是以為自己是導演,滿肚子氣,我只把自己當成一個普通人。」
「生意怎麼樣?」
「很好。」桂治洪說:「我拚命在薄餅裏加味精。墨西哥人沒吃過,覺得很鮮美。吃完了餅口渴又拚命喝可樂。我當然不告訴他們下了味精,不然他們一聽到MSG就大驚小怪。反正我沒有害人就是。我說下的是中國糖Chinese Sugar。他們都說好吃。」
我問桂治洪導演:「你到美國開始就到洛杉磯開意大利薄餅店?」
「我從香港去佛羅里達找我老婆,她說是先把我們的儲蓄拿去開中國餐館。到了那裏一看,哪有甚麼餐館?錢都被她吞了。」
「後來呢?」
「後來輾轉到了洛杉磯,打開報紙找工作,看到有公司請送碧薩的工人,就去應徵。一送,就送了一年。」
「送一年貨就有錢開店?」
「哪有那麼簡單。」他笑了,「薪水剛剛好夠開銷罷了,後來和公司的一個主管研究,他說反正開的是連鎖店,如果我有興趣投資,再做一年才夠經驗。這期間,我被黑人搶過三次,他們假裝訂碧薩,送了去,四個人包圍著我,用手槍指著我的太陽穴,拔開撞針,手一震,子彈便會射出。」
我嘆了一口氣,桂治洪卻笑著繼續說:「還算我老婆有良心,把我趕出來的時候給了我三萬塊。我一直不敢去動用它。主管說開店要十萬,可以用它來做頭一半,其餘的分期付款,就這麼有了自己的店。」
「開了店又有沒有被人搶過?」
「當然有啦。我現在有兩枝手槍,一枝放在櫃台後,一枝在廚房,都把子彈上了膛,隨時發射。星期六生意特別好,關店的時候,拿了手槍,先去街看看有沒有人埋伏,再一個箭步抱著錢衝進車子開走。」他形容得生動滑稽,我差點笑出來,但感到故事背後的辛酸,把咧著的嘴收緊。
「店舖前面站了很多毒販,賣可鹼因,他們是我的好顧客,我不能管他們賣的是甚麼,總之要賺錢,顧客永遠是對的。哈哈哈哈。」桂治洪笑:「現在大家都是朋友,他們叫我碧薩先生Mr. Pizza。」
「你現在開的意大利薄餅店,請了多少個人?」我問桂治洪導演。
「十個。」他說:「起初一大早五點到店裏親手擀麵,再去市場進貨,回來自己燒薄餅,送貨的請了一個黑人,他被他的同族人搶錢,用鐵棍打得滿囗是血,我替他裝假牙也花掉了幾千塊美金。」大家聽了笑不出。
「後來又有個香港理工學院的來找業餘工,又是給人打得頭破血流,馬上辭職。」桂治洪自己哈哈哈哈:「我對工人不錯,每年請他們去賭城玩,包吃包住,只是不包賭。有一年還關門一星期,到大浩湖去滑雪。現在,我已經是半退休了,到了週末特別忙的時候才去店裏幫手。」
「美國人在多少歲退休的?」
「五十五。」他說。
「你今年幾歲了?」我們是老朋友,甚麼事都照問。
「六十一了。」
想起當年邵氏公司派桂治洪和一班攝影師和燈光師到松竹片場實習。我帶他坐火車吃拉麵,他才是二十出頭的小伙子。
「你對電影一點也不眷戀嗎?」我問。
「做導演的願望是沒有的了。」他俯首,但即刻又把頭抬高:「我還是一有電影就看的,美國迷你戲院二十幾家都集中在一個場子裏,買一張票,東看一部西看一部,他們也不會去管你。所有的戲我都看過,香港片子我租錄影帶回家看。」
「現在看一部電影要多少錢?」
「四塊兩毛五。」
「那麼便宜?」
桂治洪笑著:「普通人七塊七毛五,我們便宜。別忘記,過了五十五歲就是高齡市民了。」
當年我帶隊,到馬來西亞的一個叫蘭交夷的小島上去拍戲,島上雨水受污染,整隊人都得了肝病。
「只有那兩個燈光和你沒事。」他說完笑了:「都是因為你們喝酒的關係。」
談到喝酒,我又想起時常開桂治洪的玩笑:話說他染了肝病後,我帶他去看一個做醫生的同學。
醫生問他:「桂導演,你喝不喝酒的?」他搖頭。
醫生又問:「桂導演,你抽不抽煙的?」他又搖頭,醫生再問:
「桂導演,除了你太太之外,你有沒有女朋友?」
他再搖頭,醫生懶洋洋地:「桂導演,你還是死了吧。」
「你現在吃飯的時候還帶不帶自己的碗碟?」我問。
自從得到那個病後,他的飲食特別小心,甚至弄到有一點潔癖的地步。
「不必了。」他說:「不過得到了肝病。到四十歲左右,就會變成肝癌。」
「你也有肝癌?」我吃驚。
「唔。」他點頭:「開刀開了兩次,手術很成功,現在一點事也沒有。」
「在美國開的?」
「不,不。」他說:「我才不在美國做手術,跑到台灣去開刀。」
「為甚麼去台灣?」
「心臟病的話,在美國開最好,美國人每一個都吃得胖胖地,心臟毛病太普遍了。醫生開刀開個不停,自然有經驗,所以比其他國家的醫術都高明。心臟病台灣不行,你沒看胡金銓導演就是在台灣開刀開死的嗎?至於肝病,美國人很少患,他們都認為這是東方人專有的,怕得要死。台灣就不同,患肝病的人多,替我開刀那個醫生是台灣第二把交椅的,你要是有肝病的話,我介紹給你。」
「呸呸呸。大吉利是。」我大罵。
他笑了,好像已經報了我開他玩笑的仇。
「現在兩個子女都長大了吧?」我問桂洽洪。
他說:「兒子唸電影,剛剛畢業。」
當年桂治洪和我同住邵氏宿舍敦厚樓,記得他那七八歲的兒子翹著嘴,時常跑到我家,一坐下來就大發脾氣,扮成武松的樣子,說要把那個賤人殺了,我們都叫他做憤怒兒童。屈指一算,應該早就讀完大學的呀。
桂治洪見我沒出聲,解釋道:「他是相信美國的讀書方法的,結了婚,生了孩子,再去上大學,一讀七八年,我就不贊同。」
「一種米養百種人。」我安慰道。他點點頭,老朋友的話是聽得進的。
「女兒呢?」我又問。
「也結了婚生了兒女。」他說:「我買了一個屋子,好大,前後花園,有四間房,我們住在一起,每個星期天抱抱外孫女,也是一樂。」
「嫁的是洋人?」
「不。」他說:「嫁給一個越南華僑。」
「做甚麼的?」
「LAPD。」他說:「洛杉磯警察,電視上也以他們拍了一個片集。」
「你呢?」我關心:「不找個伴?」
「洋人說Stay single, be happy,單身人,快樂點,多好!」他笑了。
桂治洪明天一早又要出發了,說要回船上睡,他乘豪華客輪到處遊玩,已上了癮,每年總要坐一次到世界各國去。船上吃船上住,乾淨得很。把兒女撫養長大,自己又有一家收入穩定的意大利薄餅店,閒時弄孫,桂治洪嘆氣說自己做人沒甚麼成績,但這不是成績是甚麼?比起拍賣座得獎電影但又不安的人生,滿足矣。
看著他的背影,我祝福。
摘自:《蔡瀾的豬朋狗友》 作者:蔡瀾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lovechang 的 bbs 電影板精華區
Copyright © 昔影.惜文. Template created by Volverene from Templates Block | Blogger Templates | Best Credit Card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