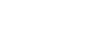發信人: "1877" , 看板: movie
標 題: [轉綠] 周黎明逐段點評《人工智能》
發信站: OpenFind 網路論壇 (Thu Jan 30 20:32:41 2003)
周黎明逐段點評《人工智能》作者:周黎明 來源:網易影視頻道
沖著斯匹爾伯格的大名和《人工智能》的片名而去影院的觀 眾多半會大吃一驚。不錯,《人工智能》的取名 酷似斯氏的名作 《外星人》,兩部都屬於科幻影片,片名都可以簡化為短短兩個 字母:《人工智能》是 《A‧I‧》,即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縮 寫;《外星人》為《E‧T‧》,乃"extra─terrestial"的縮寫。
但《人工智能》沒有一股暖流湧上心頭的溫馨,從情節上 看,它幾乎是《外星人》的對立面。《外星人》中 的小孩千方百 計把古怪的外星人送回家;《人工智能》中的人類卻把可愛的機器人小孩拋棄在森林裏。看完 該片,筆者最強烈的感受是:這原來是一部披著斯匹爾伯格外衣的斯坦利‧庫布裏克作品。
電影大師庫布裏克已於1999年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後15年裏一直醞釀著這部影片,並通過電話和傳真跟斯匹 爾伯格反覆切磋,他也曾提出由斯氏來執導筒。但由於當年的電腦科技不夠發達,這個項目被耽擱下來。庫氏過世後,斯氏接過庫氏構思的大量草稿和草圖,並20年來首次揮筆撰寫劇本,以完成前輩的遺願。這也是他拍完《拯救大兵瑞恩》以來的第一部作品。
看銀幕上的成品,《人工智能》應該非常忠實庫布裏克的原意。庫氏的作品向來需要"遠距離"欣賞,在推 出的 當年,不僅普通觀眾反應平平,連奧斯卡評委都不太賞識;但時間越長,這些作品的生命力越加旺盛。人們驚嘆它們的深刻思想性和高超藝術性,忘記了這些不朽名片在當初都屬於"有爭議"的作品。
斯匹爾伯格屬於"遠近咸宜"的電影大師,他的商業片屢屢破票房記錄,他的藝術片(至少是成功的那幾部) 能震攝任何階層的觀眾,讓每個人都潸然淚下。庫氏因素使得我們無法預測《人工智能》在短期內的受歡迎程度,但無論票房和口碑如何,兩位大師通力協作創造的巨制猶如兩顆星球相撞,爆發出憾天動地的震顫。
這不是一種和諧的聲音,如同用非調性手法譜寫貝多芬第五交響樂,因此它會讓期待一個優美童話的觀眾失望。這不是一部麻痹神經、刺激感官、過山車之旅似的好萊塢大片,它刺激的是你的智商和靈魂,因此,把《珍珠港》視為經典作的觀眾也會失望。
《人工智能》超越了所有好萊塢電影的教條和俗套,就像60年前的《公民凱恩》那樣,它讓按步就班套用現存審美準則的人覺得渾身不舒服。從命題上講,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類比的影片是庫氏的《2001年太空漫遊》。但《人工智能》的命題更為宏大,它從科學、文學、哲學、宗教、倫理、人性等多個角度同時切入;
它並沒有像絕大多數電影那樣提供一個完美的解答,但它能把如此眾多的議題有機地融合在一部戲劇作品中,這本身已是巨大的成就。我相信,不出50年,電影學院的課堂裏將會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分析該片的技巧,更會有不少博士論文試圖全面挖掘該片的奧祕。
對於筆者來說,該片讓我無法用平時寫影評的方式加以評論和介紹。如果說欣賞一般好萊塢影片只需要初中一年級的智商,本片至少消耗掉我探討100部商業片的腦細胞。我不敢說已經"吃透"了影片的內涵,但我願意以逐段點評的方式描繪一下跟該片"第一次接觸"的印象。
●第一幕:微妙的未來性、徹底的反傳統
從故事性質講,《人工智能》是一部純粹的科幻影片,裏面的故事發生在一個未明確界定的未來。我覺得時間的模糊性設置非常巧妙,因為一般科幻作品選用某個未來的年份,目的是為了強調未來色彩,而真正有效地體現未來性,是靠美工的想像力。從另一個角度講,若在2001年上演一個3001年的故事未免太像東施效顰。
在那個時候,全球變暖已導致冰川溶化,沿海城市被淹,地球資源匱乏,因此需要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制度。與此相關,大量繁瑣的工作已由機器人取代,甚至連性服務也不例外。那時的機器人從外形上已酷似人類,但每個機器人只有特定的功能,從事指定的工作,似乎少了一個"靈魂"。位於美國新澤西州的 Cybertronics公司計劃改變現狀,開發一個能付出感情的機器人小孩,以滿足不能生孩子或沒有生孩子指標的父母。
影片以該公司某教授召集員工開會、宣佈這項計劃來開場。有趣的是,在會上,一名員工立即正面提出了這項舉措的倫理涵義。在大家熱衷討論"克隆人是否合乎倫理"的今天,影片的處理可謂開門見山、一針見血。但影片並沒有停留在這個階段。
兩年後,第一個機器人小孩問世。該公司為了測試需要,從員工中找了一個獨生子患絕症被冰凍起來的家庭。這個機器人小男孩就是本片的主角──大衛,當他出現在這對領養夫婦眼前時,鏡頭從極度的"虛"慢慢變實,一個身穿白衣的男孩向前走來,似乎隱喻著他天使的本色。
大衛是個乖巧的孩子,但他在新"父母"面前會問出不恰當的問題、發出不自然的笑聲,做出不合情理的事情,顯示他仍是個機器人。原來,大衛的感情開關仍未打開,這個開關需要媽媽莫尼卡按住大衛的後腦勺,按照預定順序說出七個密碼詞才能開啟;一旦打開,大衛就無法停止他的愛,而且,你不能關閉這項功能,也不能將大衛轉售他人,唯一的脫手方法就是送回公司銷毀。
莫尼卡在兒子康復無望、企盼得到一個能交流感情的兒子的心情下,終於打開了大衛"愛的源泉"。這時, 大衛那原本光滑得像木雕的臉上,閃過一絲微妙的"復活"表情,他開口叫了一聲"媽媽"。
這一剎那,不僅大衛的性質變了,關於影片主題的爭議也像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再也無法收縮成一個賀卡詞那麼精緻的答案。大衛只是一個會叫 "媽媽" 的機器人嗎?他的愛只是一個程序的體現嗎?人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是有機體還是人性?當造物主要求被造者付出無條件的愛時,造物主對被造者有什麼樣的責任?
更直接的議題是:在人和機器、真和假之間存在著一道清晰的鴻溝嗎?我們知道邁克爾‧傑克遜的臉是"假"的(無數次整容的結果)、波霸的胸脯多半充滿了硅,而原本沒有生命的東西必將越來越"真",如 當代童話《玩具總動員》想像了一個玩具成活人的動人故事,而前陣子流行的電子寵物只是機器向人轉變的第一步,而且是極小的一步。
莫尼卡和大衛的交往可視為人類和機器相互靠攏的一種嘗試,他倆之間的母子關係處理得很微妙、很真實,沒有半點圖解大道理的痕跡。傳統童話的深度大概到此就打住了,但在《人工智能》中,這只是鋪墊而已。
不久,莫尼卡的親身兒子馬丁因為某種新藥或治療方式,起死回生,重新回到父母身邊。他對 "假兒子" 分享母愛當然心存妒忌,但影片對兩個兒子及父母的"三角關係" 並沒有臉譜化,而設計了三個細節:一是本可以不吃不睡的大衛,在馬丁的鼓動下,強迫自己吃菠菜,以適應正常生活,結果弄壞了自己體內的電路板;
二是馬丁勸說大衛去剪一縷莫尼卡的頭髮,說這樣大衛才能得到更多母愛,結果差點被人誤解為他有殺人企圖;第三次是大衛在游泳池旁遭到一幫小孩的戲弄,他尋求馬丁的幫助,結果不小心兩人都跌落游泳池,差點送了馬丁的命。
莫尼卡夫婦鐵定了心,要把大衛送回公司。在驅車前往的路上,莫尼卡稍微軟了一下心,把他遺棄在樹林裏。那是一片酷似《外星人》中場景的森林,當大衛得知母親要拋棄他時,他苦苦哀求,但莫尼卡還是含淚離去。黑暗的林子裏,只剩下大衛和一只會說話、會走路的玩具熊,還有就是大衛對母愛的渴望。
至此,影片從結構和寓意上都像是一部灰色調的《外星人》。有些影評人表示只能夠接受這一部份,因為後面的內容更像是進入一個無底的深淵,沒有一把現存的尺可以丈量。
●第二幕:令人作嘔的敵對和迫害、令人深思的立場和理念
莫尼卡拋下大衛前,說了一句"對不起,我沒有事先告訴你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影片的第二幕就把我們 帶到了這個"外面的世界":當時的人分為兩類,一類是真人,原文叫做"奧嘎"(orga),是"organic"(有機物)的縮寫; 另一類就是機器人,叫做"麥卡"(mecha),是"mechanical(機械物)"的縮寫。
從外形上看,麥卡已非常接近奧嘎,但他們在奧嘎世界的地位如同非法打工的外籍人士,時時刻刻受到歧視和騷擾,特別是有些極端份子把麥卡當作人類往虛假世界墮落的罪魁禍首,因此把流落在外的麥卡抓起來銷毀。
影片男配角在此處亮相,他是一名頭髮油光發亮的麥卡,專門為寂寞的女士提供性服務,外號為"男妓阿喬"(Gigolo Joe)。阿喬見客那場戲不僅為全劇提供了輔助性笑料,更暗示了科技進步和人類原始衝動之間的緊密聯繫。(誰能否認錄影和互聯網的普及都缺不了色情這項催化劑?)斯匹爾伯格的作品從未涉及"性"這 個兒童不宜的話題,本片的處理也絕不嘩眾取寵,即便是大人帶著小孩觀看,也不會尷尬。當然,本片並不適合兒童欣賞。
話說大衛在林子裏,看到一輛垃圾車扔下一大堆麥卡的殘臂斷腿;不一會兒,一群麥卡前來獵尋可以修補的"器官",他們不斷地嘗試那些丟棄的器官,看看是否合適。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進一步強化了造物者責任這個命題。
惡夢還在後面呢。一隊誓言消滅麥卡的"打假者"前來搜捕,大衛和阿喬都被抓走。此處,筆者注意到,搜捕隊出現在黑暗的森林時,首先是刺眼的燈光。強烈的白光在斯氏的科幻影片中一向是正面形象的化身,因為那些影片中的外星人都是友善的。《人工智能》中的強光可謂對斯氏意像的反動,它象徵著一股毀滅性力量。
大衛和阿喬被帶到一個露天體育館,那裏正在上演銷毀麥卡的血腥表演。說"血腥"並不準確,因為奧嘎把那些缺胳膊斷腿、腦袋不全的麥卡捆綁在舞臺正中,由四周的奧嘎拋擲物品,如能打翻麥卡頭頂的鐵筒,筒裏的硫酸便會滴落,化解底下的麥卡。並沒有血,但那臉皮駁落的樣子非常恐怖。
影片在這裏設計了一個只有面殼的中年婦女麥卡,她對大衛似乎有一絲眷戀。在她被推上"斷頭臺"前,她請求跟大衛說聲再見。當她的"屍體"被拖下臺時,筆者腦海裏閃過一個類似的形象,那就是《辛德勒名單》中的紅衣女孩。正如那紅衣女孩可理解為辛德勒的最後一絲希望,這位中年婦女也可理解為母性的一種投射。
在她被拖下臺時,你能感覺到區別開人和機器乃是徒勞之舉,因為人性是相對的。從科學意義上講,有些人是百分之百的"奧嘎",但他們缺乏最基本的人性(如希特勒之流);而麥卡的體內雖然裝滿了金屬和電線,但當他們能夠進行感情的交流時,他們的性質是否已發生了本質的變化?
古羅馬有過角鬥士表演,我國曾有過文革批鬥會,誰說未來就不會有打擊麥卡的群眾大會?這只是《發條橘子》剖析的暴力心態的又一種表現。大衛和阿喬經過一波三折,最後也被押到臺上。千鈞一髮之際,臺下有人注意到大衛在呼救;他說,他從未見過會乞求生命的麥卡;主持人答道,那是麥卡善於偽裝,因此更需要置他們於死地而後快。最後,因觀眾"倒戈",大衛和
阿喬才得以脫身。
影片中還有很多小細節,我們在此不便詳述。憑斯氏的敘事技巧,劇情絕不會像胡同裏扛木頭,一杆捅到底。若有人以為本片的手法就是把麥卡塑造成好人,把奧嘎寫成壞人,那就太簡單化了。
那種追求同化的心理、對歸屬的需求、對外來力量的排斥……這些不僅是人類所有的共性,其他世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你若覺得此處觀眾席上的奧嘎太過殘忍,不夠真實,他們其實是莫尼卡一家的變異。我們如能理解莫尼卡那具有人情味的歧視行為,進一步想像那些具有滅絕性的歧視行為也就不難了。
●第三幕:進入空靈和羽化的無人境界
《人工智能》的第三幕不像上述第二幕那麼壓抑,它那插上幻想翅膀的劇情充滿著沉澱淀的哲理意味。
大衛想起莫尼卡曾為他念過匹諾曹的童話,他發誓要找到藍衣仙女,請她把自己變成真正的孩子,"這樣媽媽就可以愛我了"。他和阿喬先來到胭脂城,在一個咨詢處打聽到藍衣仙女的下落。
接著兩人飛往紐約曼哈頓,那時的曼哈頓仿佛是孤島水城,只有一些摩天大樓的上面一截還露在水面上。大衛來到一幢高樓,找到了一家公司,見到了他真正的"父母親",即 Cybertronics公司的教授。原來該公司預感到大衛的行蹤,故意在問詢處留下蛛絲馬跡。
教授興奮異常,他告訴大衛說,全公司的人都很想了解大衛的遭遇。當教授前去召集員工時,大衛發現了一排排跟他長得一模一樣的麥卡小孩。正如教授所說,他不是獨一無二的,但他是"頭一個"。大衛的"人生觀"受到挑戰:所有的父母都說自己的孩子是獨一無二、舉世無雙的,但他只是一個可以不斷複製的生產線產品。"媽媽"怎麼會愛他呢?他坐在窗臺上思量著,絕望地跳進汪洋中。
以上心理活動並不是出自旁白,而是筆者的理解。該片的第三幕是抒情的"慢板",像典型的庫布裏克片那樣具有大量的"留白"。以為這又是一部《侏羅紀公園》的觀眾恐怕早就睡著了,或者出去嚷著要退票了。的確,第三幕的節奏很慢,但那不等同於拖拉,因為到這裏,影片的娛樂性越來越弱,思辯性越來越強。影片進入了哲理和童話交相輝映的禪宗境界。
大衛在水中隱約看到了藍衣仙女。他返回水面,告訴阿喬。這時,追兵趕到。阿喬在被抓走時,說了四個具有無窮玩味的字:"I am‧"(稍頓)"I was‧"借用"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的譯法,此處可譯為"我在。 我曾在。"筆者的理解是:"我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然後他意識到自己的命運,便從未來的角度補充道:"我曾經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
當然,此處的"人"應出自人性的角度,而不是有機或無機的區分。希望精通笛卡爾的朋友能提供更為詳盡而準確的詮釋。
大衛駕駛著那架水陸空飛機,在海底找到了紐約一家著名遊樂場,裏面有匹諾曹故事的雕像。他停留在藍衣仙女的像前,不停地祈求著:"請把我變成一個真正的孩子!請把我變成一個真正的孩子!"直到飛機的電池耗盡、燈光熄滅,直到又一個冰川紀來臨……
鏡頭緩緩從大衛拉出,我們的視線也消失在汪洋底下和淚水之中。
●"光明尾巴"有得有失
筆者認為,影片應該在這裏結束,因為後面的情節無論從戲劇張力還是視覺衝擊力來看,均有點"壓不住"。也許這就是好萊塢非明文規定的大團圓結局,也許庫布裏克不會同意這畫蛇添足的 一筆(但他的《2001年太空漫遊》也有類似欲罷不能的結尾)。
總之,這個並不光明的"光明尾巴"只能讓人感覺好受一點,但無助於情感的昇華(catharsis),遠沒有雕像和大衛連同全世界都被冰封的畫面效果,沒有那種文藝作品進入最高境界時受眾和戲劇人物之間產生的高度情感交融(pathos)。不過,從純科幻及心理學角度講,這個結局仍頗有嚼頭。
又過了兩千年,人類也徹底消亡了。另一種形體仿佛出自馬蒂斯繪畫的高級動物成為地球的主人,他們從飛機裏找到了大衛,並想從他那裏了解人類的歷史。對於大衛想再見到"媽媽"莫尼卡的願望,他們願幫他實現,但有一個難題:那時的科技能通過基因複製人類,但復活的人只能活一天。大衛答應了,並從小熊身上找到莫尼卡的一縷頭髮。
他又回到了原來的家,看到媽媽蘇醒過來。那一天,母子倆生活在一個沒有嫉妒、沒有憂慮的世界裏。晚上,當媽媽睡著的時候,大衛也乖乖地躺在媽媽的身邊,悄悄睡著了。
你可以說這是俄底普斯情結的優美體現,也可以說這是《綠野仙蹤》裏多蘿西跨越彩虹後找到的真諦。影片的人文積澱非常之深,編織了一幅童話和神話、科學和幻想、理智和情感的多彩畫卷。
●高難度的技巧、不和諧的和諧
影片中有許多令人難忘的鏡頭,且不乏象徵涵義,但斯氏從不為了賣弄深沉而強調這些處理手法。觀眾可以只留意它們的形式美,但回味起來卻收獲更大,如莫尼卡透過玻璃門觀察大衛那個鏡頭,畫面上出現玻璃折射的一排大衛形象,仿佛是新的生命形態給人類設置的一個謎。
第三幕裏有一個大衛眼睛的特寫鏡頭,一開始是一片白,然後高光漸漸縮小,透露出大衛充滿哀傷的藍眼睛。俗話說,眼睛是心靈的窗口。我們從他那從不眨一下的眼睛中,見證了從高明的機械到基本的人性之間的演變。那個鏡頭中的眼睛,藍得那麼純真,那麼深邃。
影片的美工不只是搭建後現代派的寓所及三輪汽車,每一個細節都散發著神奇的想像力,特別是胭脂城和通往胭脂城的橋梁,更是可以媲美《綠野仙蹤》裏的黃磚路和翡翠城。
約翰‧威廉斯譜寫的音樂吸收了大量後現代派的非調性技巧,恰到好處地起到烘托或點題的作用,但絕不"搶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在大衛祈求藍衣仙女時,音樂中隱約出現了經典動畫片《匹諾曹》主題歌"當你向星星許願時"的一個和弦。
在斯氏的作品中,演員都能發揮出自己的最佳狀態。本片中大衛的扮演者海利‧喬‧奧斯蒙特和阿喬的扮演者裘德‧洛尤為出色。說奧斯蒙特是有史以來最有天賦的童星一點也不誇張,一般的童星(如流行一時的秀蘭 ‧鄧波爾和麥考利‧考爾金)都是靠乖巧來取悅觀眾,而奧斯蒙特在最近這幾部片中全部需要高難度的演技,絕非扮天真可以打發。
怪不得好萊塢圈內人士感嘆到,以前只有解數學題或下象棋的神童,如今總算出了一個會演戲的神童。不信,你看他會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被淘汰(大多數童星都過不了15歲這個坎)。
大衛在戲中非常微妙而分階段地融合了人跟機器的特徵,隨著他跟人的交往越來越多,他的機器特性逐步削弱。裘德‧洛的表演沒有奧斯蒙特那麼可圈可點,但這位英國大帥哥對喜劇的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演繹了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浪漫英雄和未來貓王的綜合體,諧趣而不油滑,使人物起到了絕佳的陪襯和對位作用。
本片的模型和電腦特技無處不在,但不像那些恐龍那麼顯眼,光是那只玩具熊,著名的工業光魔公司(ILM)的 專家就投入了最優秀的人才。無庸質疑,斯匹爾伯格的幕後創作班子必定是好萊塢一流的,他們曾經得到的奧斯卡小金人若是加起來,大概需要幾個籮筐才能裝得下,看來這回籮筐又得加大了。
兩個長相截然不同的父母生出來的孩子,如果長得好看,父親那一方會認為小孩像父親,母親那一方會說像母親;如果認為不好看,則自然把罪責推給對方。庫布裏克的崇拜者可能會不喜歡斯匹爾伯格的處理,斯氏的追隨者可能會覺得影片不夠親切煽情。由於《人工智能》是一部大膽創新的冒險之作,不是一部四平八穩的規範之作。
筆者以為,本片中庫氏和斯氏的結合,是宏觀和微觀、神和形、冷和暖、慢和快、腦和心、理性和感性、思辯和直覺、超然和入世的結合,之間有矛盾是必然的,在這種矛盾產生的不和諧是一種高度藝術化的不和諧,是更高層次的美。觀眾從人物(包括機器人)的細微末節感受到人性的力量,然後再作用於理性,從而啟迪對萬物的思考。
人生本是一個探索和追求的旅程,《人工智能》如同一面魔鏡,照射出每個人內心的騷動、恐懼、渴求和憧憬。跟那些侮辱觀眾智商、按機械模式生產出來的好萊塢大片相反,它為你打開了一扇通向靈魂深處的 門。《人工智能》是一部電影藝術的曠世傑作。(zhouliming@hotmail‧com)
關於A‧I‧:給周黎明的一封信
作者:熊菂 來源:網易影視頻道
周黎明,你好!
很喜歡看你在網易上的影評文章。最近這篇"周黎明逐段點評《人工智能》"也寫得很好,還幫助我明白了看電影時沒看懂和忽略了的幾個小細節。但有一個細節,看過你的文章後我覺得你也忽略了。就是你文章中提到的在露天體育場,對大衛表現出一絲眷戀的那個殘缺不全的婦女。
你沒發現嗎?她實際上就是影片一開始,教授向人們展示的那個代表了最新科技的女機器人哪!才不過幾年,她就已經過時而且破成那樣了。我想這是否在影射甚至諷刺如今電腦越來越迅速的更新換代?
記得當時看完這部電影,我還不明白如果不喜歡"領養"的機器人為什麼要送回原公司銷毀?為什麼原公司不改裝一下找下一位"買主"?多麼浪費!也是個科幻迷的丈夫說:這其實跟現在人們對待電腦的態度一 樣。在 386、486、586迅速更新換代的時候,誰還會費心去改裝一臺286呢!那些流浪的機器人也許就和街邊扔掉的一 臺286電腦一樣,在人類眼裏沒有任何"價值"了吧!
安排這樣一個女機器人我覺得值得玩味的地方還很多。在影片開頭,教授問她"愛是什麼",你記得嗎?她的回答是一段長長的背辭典般幹巴巴解釋。但到影片中段,她即將被毀滅時對大衛表現出的保護和不捨,清清楚楚是一種感情,一種感性的、人類的感情。也就是說這二十多個月,不知她經歷了什麼、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但她已經懂得了愛。
就像你說的這部影片"留白"還很多,夠人們慢慢發現討論的了。不過這個情節挺重要,並且你的文章正好涉及了,所以我冒昧地寫郵件來跟你探討一下。
還有一點小意見我想要補充:就是在影片開頭,面對"人類給機器人製造出感情讓機器人愛人類,那麼人類能不能回報以同樣的感情"的提問,教授的回答是:上帝在製造亞當的時候並沒要求亞當愛他。言下之意:人類愛機器人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上帝愛人類,人類也愛上帝一樣。這實際上是把自己擺在了上帝的位置。
這也是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倫理問題: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能力的不斷增強,對自我認識必然不斷膨脹。當人類也能象上帝造人一樣創造出帶"生命"意味的事物時,人是否已經挑戰了自然的權威?更危險的是,人類真理解生命的涵義嗎?當他們批量生產著所謂的具有"感情"的機器人時,他們以為他們在創造生命了。
但正如你文章中所說的,生命之所以可貴正在於其獨一無二性,不可替代性。影片這樣的結尾,以一個由人 類 製造出來的機器人做為外星人眼中人類的代表,是否證明了人類企圖"成為"上帝的失敗?
人類其實並不具備上帝的胸懷和能力,到最後,地球仍然存在著,只不過換了居住者;海洋依舊存在著,只不過結了冰,連那個渴望成為真正的人類的小機器人也存在著,只不過在海底靜靜沉睡著。只有人類,人類沒有了蹤跡,只能從小機器人的記憶中打撈出些許蛛絲馬跡,這不是個巨大的諷刺嗎?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lovechang 的 bbs 電影板精華區
Copyright © 昔影.惜文. Template created by Volverene from Templates Block | Blogger Templates | Best Credit Card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