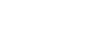發信人: armida@bbs.ee.ntu.edu.tw (armida), 看板: movie
標 題: 【轉載】在紐約看《英雄》(轉載)
發信站: 台大電機 Maxwell BBS (Thu Jan 23 16:49:50 2003)
在紐約看《英雄》 張旭東
去年九月底在紐約看了張藝謀的《英雄》,是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為市場調查而搞的一場內部放映。電影結束后,偌大的劇場里觀眾黑壓壓一片,都在低頭填那份長長的問卷,場面有些奇怪。因為剛剛看完,強烈的視覺印象還堆在腦子里,既無法也不想集中精力細讀表格上那些囉嗦的問題,所以填得很偷懶。不想走出劇場,一眼就看見導演本人就站在門口。
我兒子自小看過不少張藝謀的片子,自從知道張藝謀也要拍武俠片,就一直等著,現在總算如愿以償。他剛說覺得《英雄》比李安的《臥虎藏龍》更過癮,一聽見眼前這位穿大紅夾克的中國人就是 ZhangYimou 本人,就走上前去和他握手,還用他那英文句式的中文對張藝謀說“我喜歡你的電影”。我和愛人,連同一道來的几位同事和朋友便也都紛紛跟他打招呼。不過張藝謀在這种場合顯得有些不自在,也沒有心思就片子多說什么。
我們几個卻在回家的路上談了一路。
《英雄》明顯是一部准備在全球發行的商業片,首先是沖著“好看”拍的。在這個意義上,它無疑是成功之作,除了片中從塞外大漠跳到桂林山水的旅游風光集錦也許會讓中國觀眾覺得好笑。三千萬美元的投資,折合成兩億人民幣,在中國電影業是個大數目。但以好萊塢大片的標准,衹能算中小型預算。但張藝謀之為張藝謀,就在于無論拍什么都得在每一個畫面上打上明确無誤的個人風格標記。
也就是說,《英雄》又必然是一部法國人所謂的“作者電影”。在今天的好萊塢,能把動作片拍出個人風格的,或者說在一种視覺藝術的高度上拍動作的實在沒有几個人。值得一提的是,這里面中國導演就占了三位:吳宇森 、李安,加上新到的張藝謀。
從張藝謀個人記錄看,《英雄》和當年《代號美洲豹》那樣 試“娛樂電影”的敗筆不可同日而語。無論就我自己作為普通觀眾的第一感,還是從劇現場气氛來看,《英雄》在美國電影市場獲得《臥虎藏龍》式的成功,應該不成問題。
《英雄》的商業片邏輯在此不談。作為張藝謀作品,在電影史的意義上,我首先注意的是作者与其他三位導演的競爭關系。他們是:李安、陳凱歌、黑澤明。
李安的《臥虎藏龍》風靡國際,幵創學院派藝術電影和通俗電影類型(武俠片)結合的成功範例。張藝謀沿此路向前探索,但自成風格。兩部片子都以身怀絕世武功的主人公“放棄”我告終,都帶有“反武俠”的“超越性”。
但《英雄》与《臥虎藏龍》相比,顯然是要以闊大胜纖細、以強烈凝重胜輕柔飄忽,以“英雄”胜“俠士”、以“天下”胜“江湖”、以集体責任胜文人情調,以体現于王者事功的道德秩序胜個体生命的虛無主義体驗 。兩片在其超越性的价值指向上又迥异其趣。面對兩部同樣具有“中國气派”的國際化藝術功夫片(姑且這么稱呼吧),觀眾衹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最終是“蘿卜白菜,各有所愛”。
張藝謀和李安的這層競爭關系最直接,最表面,最具体,貫穿于整部影片,甚至決定了許多場景的設計和色調。這是一种友好的競爭,因為它拓展了此類電影的風格空間,有點像武林中“南拳”對“北腿”,各有所長,彼此不傷和气。章子怡出現在兩部影片中,也像是對這种友好的競爭性戲仿(parody)的提示。
不過,友好歸友好,張藝謀在《英雄》中表現出來的強烈好胜心和對自己個人風格的不懈追求還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它使得《英雄》最終遠遠超出了和《臥虎藏龍》的競爭關系,而在意象、場面設計、結构安排、敘事推進和道德寓意上能夠博采眾長而又多有創意。
比如影片幵始不久,無名和長空以古琴伴奏的雨中打斗,既有中國古典空靈之美,又結合了好萊塢科幻電影(比如《駭客帝國》中的時空伸縮特技,整個場面一气呵成。秦軍弓箭隊的儀式性陣法和毀滅性攻擊則是張藝謀自《黃土地》里面的群眾場面(腰鼓、祈雨)和《紅高粱》以來“偽造傳統”(顛轎﹔造酒)制造視覺奇觀的又一絕活。
与陳凱歌的競爭就复雜得多,因為這分明是兩种不同的電影語言和風格、不同的藝術理念競爭,最終是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不同理解間的競爭。陳凱歌曾是“第五代”或“中國新電影”的代言人。他的《黃土地》和《孩子王》一直被視為第五代電影的標志性作品。
作為陳凱歌的攝影師,張藝謀為第五代電影語言的确立作出极為重要的貢獻。但從他執導的第一部電影《紅高粱》幵始,張藝謀在藝術觀念和藝術實踐上就和陳凱歌分道揚鑣,隨即在“新電影”內部形成分庭抗禮之勢。這似乎是當代中國電影史上的公論。
事實上,在《霸王別姬》和《活著》這兩部電影中,兩人之間的競爭就已經十分明顯:前者是“為藝術而藝術”的天鵝之歌,表達了藝術家個人對現實的看法和審美自律性的向往﹔而后者則在歷史事件的無情交替中強調普通人日常生活本身的史詩性。
在九十年代中期,這种區別還僅僅具有電影美學上的微妙含義(兩部片子也几乎同時在西方主要電影節上獲獎),但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今天,這种區別則可以被用來作為測量當代中國文藝界和知識界立場分野的一個標准。
此后,張藝謀在《秋菊打官司》里達到一個藝術上的高峰,在風格、敘事和倫理立場上取得一种當代中國電影界無人比肩的成熟和定型能力。与此同時,陳凱歌的電影語言則一再陷入危机之中。
如果可以把第五代的歷史簡化為陳凱歌和張藝謀之間的競爭史(這當然衹是一种批評的抽象,就像阿多諾曾把整個西方現代音樂的歷史“簡化”為勛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之間的競爭),那么公允之論應該承認,至少到目前為止,張藝謀對陳凱歌取得了壓倒性优勢。
張藝謀這次在陳凱歌拍《刺秦》之后用相同題材拍《英雄》,說明他還是很把陳凱歌放在心上,更确切地說,他似乎認為,表明自己与這位第五代老戰友之間的分歧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第五代導演對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情有獨鐘(此前還有周曉文拍攝的《荊軻刺秦王》,由姜文飾嬴政),并不奇怪。畢竟秦滅六國,“書同文,車同軌”,綿延一兩千年的封建大一統由此确立,是中國歷史上幵天辟地的大事,可謂中國古代政治化的源頭之一。荊軻刺秦王的故事經太史公如椽巨筆,早已具備民族神話的資格。
這對試圖以“現代電影語言反思民族歷史文化,重寫民族神話的“第五代”導演來說,具有天然的誘惑力。對這樣的“事件”或“題材”,當然應該有不同的解釋和處理,它們之間的分歧和沖突理應視為當代中國自我認同的內部矛盾和沖突。不如說,衹有通過這些解釋的沖突,當代中國的自我 認同才能夠源源不斷地被“生產”和“發明”出來。
陳凱歌的《刺秦》對秦滅六國和秦王嬴政本人都作負面處理,取向基本上是基于當代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原則,譴責暴力,將暴君和宮廷政治心理化、精神分析化、丑角化。在統一問題上,陳凱歌的片子同情六國義士而排斥民族國家的“天下觀”,強調權力內在的腐敗、武斷和殘暴。但符合西方价值觀念的東西不一定就在當代西方文化市場上受歡迎。
陳凱歌電影語言的形而上和說教傾向恐怕起到了隔絕劑的作用。如果陳凱歌衹愿意用緩慢、夸張、不斷停頓、划滿了著重號和惊嘆號的電影審美造型來傳達歷史批判和文化批判的信的話,觀眾看到的就衹能是藝術家的自我形象矗立在鏡頭前,遮擋而不是打幵了一個廣闊的影像世界。
反觀張藝謀,《英雄》的主題不可謂不大,但它不是基于某种普遍性的抽象原則,而是運行在中國歷史文化心理的獨特脈絡之中。它的藝術展幵不是沿著“一般的個体性”所認同的普遍价值,而是同中國歷史脈絡本身的矛盾及其展幵有某种對應和共鳴關系。這种不同決定了陳凱歌的《刺秦》是一個閃爍其詞的象征主義迷宮,而張藝謀的《英雄》則是一個生机盎然、大刀闊斧的寓言故事。
張藝謀以《英雄》這樣的商業片回應陳凱歌的哲學說教不無諷刺意義。用攝影机進行文化歷史沉思不是張藝謀所長,也不是他喜歡做的事情。而武俠片的架构則從電影類型上規定,電影作者必須用“講故事”的手法,以場面、動作、運動和事件的發展作為電影作品基本要素。
深具平民意識的張藝謀好像意識到,在處理重大歷史事件上的立場上,《英雄》 國內政治環境中雖居主流地位,并且在社會心理上同某种民族潛意識遙相呼應,但在國際語境里,卻無法以高調知識分子語言做正面的藝術和思想上的發揮。
因為當今國際大環境給出的選擇,好像不是前南斯拉夫式的以“族裔自決”肢解國家,就是一古腦兒地加入“全球市場”、“世界政府”、“普遍人權”。夾在中間的那些在歷史中形成的民族國家,特別是有較強的文化傳統、國家能力和民族向心意識的國家,几乎都在強勢意識形態的高壓下有口難辯。
在這种情況下,商業片這种全球文化工業的主流形式就變成了一個自然的選擇。武俠電影這個特殊形式或許可以用視覺奇觀和情節人物把某种特殊的中國文化特性“中性化”,從而變成像美國西部片那樣的“普遍消費品”。衹是這种消費品骨子里做的也許不是美國夢,而是中國夢。
說實在,我并不認為張藝謀會考慮到如何避幵海外中國問題專家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挑剔眼光以表達某种“中國情怀”。但作為一個成熟的電影作者,他似乎本能地認為,既然《英雄》是拍給大眾看的,就自然應該用大眾看得懂、喜歡看的方式來拍。
“讓票房說話”的態度聽似很簡單,很“商業化”,很“反知識分子”,但實際上,在特殊的語境里,它可以包含很多層意思。就是說,張藝謀說這句話時針對的是當代中國的整体環境(包括國內和國際),而不是針對自以為是的知識輿論界。
在与陳凱歌《荊軻刺秦王》的競爭中,張藝謀看上去好像衹在乎能不能抓住觀眾。但實際上,抓住了觀眾,也就同時抓住了很多東西。觀眾不僅僅是消費者,同時也是讀者、父母、鄰里、同事,是當代中國社會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成員。他們是一個歷史的存在,一個傳統的載体。
如果這些“消費者”真的 在一种藝術的生活方式里体驗到一种舒暢的自由,“中國”就已經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而是一個具体的有意味的形式了。在這場大實驗中,張藝謀無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當代中國的首席電影作者。
最后,張藝謀也是在直接或間接地同以黑澤明為代表的東亞電影現代主義傳統競爭。《英雄》的敘事結构和《羅生門》看上去有點相似,即兩者都以多重敘事角度講述“同一個”事件。但這里談不上有什么模仿。首先,《羅生門》敘事結构早已是老生常談,模仿它就像把“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廟,廟里有個老和尚講故事”當作敘事技巧的創新來傳播一 滑稽。
其次,黑澤明在《羅生門》中的多角度重复敘事有強烈的形式實驗的游戲性,其哲學核心是一种不可知論。《英雄》里的几個敘事“版本”之間卻是依次推進,最終露出真偽之分。無名對秦王講的故事虛虛實實,其目的并不是展示“真實”之不可能或証明“敘事”和“表現”的“形式自律性”,而是通過形式上的重复,一層層發掘人物和事件的 內在關聯,一步步向更大更深的主題逼近。
在《英雄》里面,“現代主義電影語言”和敘事風格本身不再是中國電影“地方詞匯”削尖腦袋往里鑽的“國際形式”。它不再构成當代中國電影創造力的仲裁者,而衹是當代中國敘事想象的一個參照系。
在一層層“虛构”的帷幕去除之際,“歷史”的面目逐漸清晰起來。在這個過程中,觀眾和秦王一樣由聽(觀)眾變成了受教育者。在動作片的外表之下,《英雄》的确呈現出一個教育電影的結构。歷史寓意、民族記憶的道德訓誡、當代生活的藝術和政治想象取代了蒼白的“現代電影觀念”而成為電影敘事學和電影符號學的內容。
就《英雄》敘事結构上的重复与變化來說,張藝謀模仿的不是他人,而是他自己。在《秋菊打官司》里面,秋菊一次又一次從山村出發去逐級上訪“打官司”。每一次出發的景物、人物、音樂几乎一模一樣,但這一次次的重复所表現的并不是停滯或缺乏變化。相反,它耐心地、逐漸深入地探入了某种在變化之中不變,在种种物質、權力、符號、資本和商品的交換之中不可交換、不可替代的東西。
它在技術語言和法律條文支配的世界之外,但它正构成由像秋菊這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獨特性和本質。我們記得秋菊要的并不是賠償,甚至不是道歉,她要的不是一個現代法理學意義上的“等价物”,而是一個“說法”﹔她要的不是抽象的懲罰或正義,而是實質性的意義和生活世界的圓滿。張藝謀許多影中的女主角都异乎尋常地□,“一根筋”。這种中國農民式的倔強和堅韌推動著“重复”的敘事。
電影里秋菊的執拗努力每重复一次,觀眾就向理解那個沒有任何語言或法律條文能夠描述的“說法”靠近了一步。而每一次秋菊從外面的世界無功而返,那個被我們視為文明的基石和現代人行為准則的法律就瓦解了一次﹔而隨著它的瓦解和無效,我們發現,有一個更基本、更隱蔽、更永久的“前法律”的秩序支持著,同時顛覆著脆弱而抽象的普遍法律。
它質問法律,但它又是能使法律本身獲得意義和价值依托的唯一保証。這种東西并不認同什么“普遍性”,而衹在重复中自我顯現。重复,用當代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Deleuze)的話說,就是事物的“獨一無二性不斷地肯定自己”。它的在場表明,“靈魂沒有交換价值﹔它不屬于普遍性的國度”。
《英雄》的敘事邏輯正是這個意義上的重复。通過重复,一個寓言故事一步步逼近了它的歷史的和价值論的起源。通過重复,一种“獨一無二性”在不斷地肯定自己。一部好看的電影就像一個節日,它“重复著不可重复的東西”(德勒茲)。
法國詩人和散文家佩居伊(CharlesPeguy)曾說,不是法國國慶日在紀念和重复攻陷巴士底獄的那一天,而是攻陷巴士底獄的那一天預先在慶祝和重复法國國慶日。如果我們在《英雄》的當代性里看到了一种對古代中國的“慶祝与重复”,我們或許就已經找到了那种預先在慶祝和重复著當代中國的隱祕源頭的蹤跡。就“重复性”取代“普遍性”這一點來說,張藝謀成功地擺脫了“現代主義”對當代中國文藝的審美統治。
据聞《英雄》在國內放映后已創下票房紀錄,但也頗受一些人的批評。其中激烈者,或指《英雄》借無名之口,表達了一种“趨炎附勢的奴隸心態”﹔或對《英雄》以和平之至善的名義放棄對秦王殘暴專制的清算表示不滿。這种“誅心之論”有無根据暫且不說,其道德和政治依据卻仍然來自“作為普遍价值的自由主義”。從《英雄》到自由主義未免扯得太遠。
不過我疑心待《英雄》下個月在美國各地“閃亮出場”之時,大部分美國觀眾會本能地擁抱影片的和平主題,而根本不去管它是否盡到了號召美國以外的老百姓起來反抗當地專制暴政的宣傳鼓動職責。原因很簡單,美國現在正忙于在全球追剿恐怖主義“暴徒”,建立美式“和平、繁榮、自由”的新世界秩序,大概不會鼓勵人們去效仿荊軻的榜樣。相反,在《英雄》里面,美國的帝國想象或許能做一個白日夢,
夢見自己有了一個新名字: Tianxia(天下)。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lovechang 的 bbs 電影板精華區
Copyright © 昔影.惜文. Template created by Volverene from Templates Block | Blogger Templates | Best Credit Card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