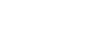作者: somnolence (不見。不散。) 看板: TSAIMingLian
標題: 蔡明亮只拍自己想拍的電影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 (Tue Dec 16 15:07:35 2003)
從拍攝第一部電影《青少年哪吒》並摘下東京影展青年導演銅櫻花獎開始,蔡明亮就一直是國際影展的常勝軍。第二部電影《愛情萬歲》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河流》奪得柏林影展銀熊獎,《洞》獲得坎城影展影評人費比西獎。
這些殊榮不但讓台灣在世界影壇佔了重要地位,也讓蔡明亮成為享譽國際的知名導演。但是上個月,他卻向今年的金馬獎說「對不起」!
蔡明亮發表書面聲明,以「評審連任、創作遭到汙辱」等原因,宣布退出國內最大規模的影展競賽,這個舉動遭到褒貶不一的評議,甚至引來檢舉,指他持馬來西亞護照,不具申請國片輔導金資格。
引發兩極評價的蔡明亮,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美麗佳人帶妳進入他的內心世界。
蔡明亮有種奇異而對比的張力,他拍電影卻害怕鏡頭對著自己,他習慣孤獨卻對身邊親友萬分掛心。就像他的電影,冷漠疏離的表情底下,躲藏著對愛的強烈渴望,巨大而又深沉陰暗的基調,其實透露著對生命的強烈期望。
你可以稱他是揚名國際的明星級導演,但更貼切的說法是-率真、誠摰、熱愛生命的電影創作人─蔡明亮。
●我覺得我像鯨魚,很孤獨,體積很大,別人不敢惹,但不會主動攻擊,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
在中影略顯狹窄的辦公室初見蔡明亮,他正在吃香蕉,接著大快朵頤的是另一盤切好的楊桃,都是他最愛的熱帶水果。在轉往頂樓會客室的路上,注意到他沒穿襪子,「我幾十年不穿襪子了,從小就不喜歡」,背著帆布書包、理個三分頭的蔡明亮說。
從馬來西亞來台灣文化大學影劇系念書,蔡明亮就常坐公車往西門町或對面的中山堂、重慶南路一帶跑,最多的時候是來看電影。
「上大學,就是讓我可以理直氣壯的看電影。到大一下,還有很多同學不知道有我這號人物」。當時,蔡明亮和他稱為「恩師」的王小隸辯論電影,也結識了焦雄屏、蔣勳等文化人。蔡明亮漸漸發現他想拍的電影和主流好萊塢式風格不同,而是要反映他周遭的環境,呈現最真實的生活。
「我拍我想拍的東西」,他提到自己很欣賞的作家余秋雨曾說:「要面對文藝、背對文壇」讓他心有戚戚,「當然,在電影圈更難做到,但至少我希望自己能既要面對影壇,又要面對創作。」停了一會,蔡明亮說:「創作,永遠是寂寞的。」
蔡明亮喜歡獨處,生活也力求簡單,不吃素,因為不想給人添麻煩。喜歡動物,最喜歡貓。「因為貓很有個性;雖然我養的流浪貓都是一叫就過來的。」但是每次貓發情又不能出去的痛苦讓他很替牠們難過,覺得應該放出去,然後牠們就再也沒回來。「現在我不養貓了,但只要看到貓就會停下來,想要靠近。」
問蔡明亮如果用一種動物形容自己,會是什麼?他大笑著說,這個問題昨天才想過。「鯨魚,因為牠很孤獨,體積龐大教人不敢惹,但又不會主動攻擊,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
昨天他和李康生、楊貴媚、苗天一起到北濱海釣,「我不釣魚,因為不喜歡殺生,但又勸不了他們,昨天正好想看海,就一起去。他們釣魚,我躺在石頭上吃了很多零食以後就睡著了,做創作的人好像每天都沒什麼事,其實心裡一直存在著壓力」。
一定常失眠吧?「對,睡覺很辛苦,之後,就開始做夢,最常夢到自己在飛,縱身一跳,就可以飛了,但都只有這麼高。」他比了個到腰部的手勢。他還會夢到各種顏色的飛碟,也做噩夢,「不知道心理學家怎麼說?」蔡明亮做個調皮的表情說。
●水是內心的暗流,是每個人心裡都有的,不能言說的祕密。
在蔡明亮的電影中,一再出現的漏水場景,除了有著很深的象徵意義,其實也是他現實生活中經常碰到的狀況。「不管我住到那裡,一定會遇到很嚴重的漏水」,曾住在花園新城的蔡明亮,有天半夜不小心誤開了一個壞的水龍頭。
「大水像橫的噴泉一樣,不管我用什麼東西都塞不住,很快的,水已經淹到客廳、房間,我感覺鄰居都聽到這種大瀑布一樣的水聲,真的很恐怖,我打電話給朋友,他說,你怎麼那麼笨,關總開關就好了,我試了還是無效,最後是水電工被我吵醒,才解決這個問題。」蔡明亮邊笑邊說,「連我去巴黎旅行,暫住的公寓也漏水,樓下的法國人還跑來按門鈴喊:你知不知道你浴室有問題!」
話鋒一轉,他談到多部電影裡的「大水」,表情嚴肅起來。「水,象徵感情,我覺得人像植物一樣,缺水就會枯萎,於是我很愛拍演員喝水、喝礦泉水,因為對自來水沒信心。
在《青少年哪吒》,水從廚房裡倒灌進來(那也是蔡明亮的親身經歷),陳昭榮不停的試圖找東西塞住,正呼應著他的內心狀態:渴望愛,但愛來的時候又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拚命阻擋。到了《愛情萬歲》,電影裡那個豪華的浴缸讓每個人都很想擁有,卻都只能偷偷的用。
在《河流》,『水』更是漫天蓋地的嚇人,這個時候『水』是內心的暗流,是每個人心裡都有的、不能言說的祕密。水,象徵電影裡同性戀父親內心的慾望,明明是同性戀又結婚生子的男人,讓整個家都不快樂。他的房間漏水,他用各種方式阻擋,結果水流到家裡的每個角落,太太也發現他的性傾向,他一個人的苦果卻讓全家人一起嚐。」
「在《洞》裡,是更大、更敗壞的環境,這部非常象徵的電影,劇情不多,是以細節舖陳進行。我用不斷的下雨象徵世紀末敗壞的大環境,一個男人(李康生),和一個女人(楊貴媚),是人類的縮影。
楊貴媚整天在和外在環境對抗,她守著家不願離開。不敵大水帶來的細菌,她也感染了病,變成像蟑螂一樣在地上爬,原先一直和他作對的李康生看到這情形都哭了。最後李康生給了她一杯乾淨的水,救她出去。『水』在這時變成人和人接觸的媒介,它是敗壞的,也是救贖的,就像是所有東西都有好多面,什麼事情都沒有絕對的」,蔡明亮神情認真的舉出電影中水的各種面貌。
「洞」是蔡明亮作品中,少見的以「H appy Ending」作為劇終。那下一部呢?原本想賣個關子的蔡明亮還是透露了一些。片名暫訂「你那邊幾點?」談一對台灣相識,但相戀後又分隔台北、巴黎的戀人故事,因為時空距離,讓維繫感情更不容易,將由陳湘琪、李康生主演。蔡明亮說,他想拍這個題材想了很久,片中會加入更多的浪漫,有別於以前的作品。
●我父親嚴肅、刻苦,從不坐下來和我好好聊一聊,你說他很堅強嗎?其實他比誰都脆弱,年老時他常常掉淚。
看蔡明亮的電影,發覺他關心的層面,從青少年到同性戀到異性糾結的感情。蔡明亮說:「我關心我周圍的人,我不覺得我有什麼使命感,創作是很個人的,一定要從內在出發,才有感覺。我所有的描寫,都和我的生活有關。其實,現在最想描寫的是人生。我不理解人生,不理解人,不理解我自己,或是我的父親,特別是我的父親。
他嚴肅、刻苦,有了錢也不懂享受,年老生了病,就走了,他從不坐下來和你好好聊一聊。你說他很堅強嗎?其實他比誰都脆弱,年老時他常常掉淚。我不明白,怎麼和我小時候看到的他完全不一樣?人不容易了解,有陰暗面,有脆弱面,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有比較包容的想法,就不容易讓自己受傷,人際關係上也會更好過一點,因為我發覺大家都很缺乏這樣的心,所以我才要用電影的方式拍出來。
曾經一個節目主持人問我為什麼那麼悲觀?我反問她,妳不悲觀嗎?妳覺得到二○○○年台北會更好?她說是,我很佩服她。我其實是用另一種更積極的態度去生活,而不是假裝沒有看到問題。
《洞》片中,我用葛蘭的歌舞貫穿全片,那是五○、六○年代生活氣息的產物,天真、熱情、直接、敢愛敢恨、沒有算計。這種純真和熱情是每個人都需要的,但現代人都太武裝自己,去追求你追不上的東西,不誠實面對你心靈的真正需要。如果『純真』存在,我就拍出來給你看。」
蔡明亮形容台灣經濟奇蹟是用「劇烈」的手段來換取進步,但過程,讓所有人都付出代價。來台灣已經廿年的蔡明亮,現在回到家鄉馬來西亞古晉城,會有種過客的心情,原本想要寫的劇本又原封不動的交了白卷回台灣,完全沒有心情工作。這個婆羅洲上的熱帶城市,在馬來語是「貓城」的意思,還有座貓博物館。
他說:「我有七個兄弟姊妹,所以小時候我媽媽不太能夠『應付』我們,就把我送去給外公外婆帶。外公愛看電影、外婆愛看小說,我就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每次要回自己的家,都會很高興,雖然想親近家人,但平常沒住在一起,總會有些距離。
和哥哥、弟弟玩耍時,他們是一國,而我只有一個人,這確實影響了我的人格,非常習慣孤獨。每天寫完功課,睡覺前,我都會花一個小時幻想這個時候,如果在外公家就會正在做什麼?這種愛幻想的性格,一直持續到現在。」
●很多人也許看我的電影覺得不舒服,我想,是因為害怕看到自己,雖然電影中我常常呈現出很不堪的生活狀態,但我「丟」了希望在裡面。
做為得到國際影展大獎的明星導演,一開始蔡明亮很不適應,緊張得連生活都亂了。喜歡上市場買菜的他,還曾經被竊竊私語的人跟蹤。「偏偏我的樣子又讓人很好認」,他拍拍自己的頭說。於是蔡明亮開始減少曝光,特別是不上電視。
「因為我害怕機器對著我,害怕拿著麥克風說話」。他幾乎推掉所有採訪,家裡的答錄機也從剛開始滿滿的通告,到現在通常是「零」,他覺得很好,生活也比較舒服,「做任何事情,不要把自己全部都賣了」。現在的蔡明亮已經慢慢適應成為公眾人物的感覺,但他還是最想做自己。
常有人問蔡明亮,可不可以換一些別的演員?但形容自己「特別重感情」的蔡明亮覺得每個人都不停的在變,他喜歡觀察並掌握這些細微的變化,所以從不忌諱用同一個演員,連技術人員也很少更換。「也許彼此都不完美,才有更大的進步空間。」
蔡明亮一再強調自己的步調很慢,很多事都不急。「大前提是要拍好電影,而不是為了參展,和我合作的人常常很緊張,我還反過來安慰他們」。但究竟什麼時候會著急?「不是著急,是操心。」他很少操心工作上的事,但只要親友出國,他一定從對方登機那一刻開始擔心,直到對方打電話報平安為止。
除了重感情,蔡明亮也是直覺敏銳的人。「我喜歡率真的人,應該說是好惡分明吧!」這其實就是他自己性格的寫照。
擅常研究命理的賴聲川曾經對蔡明亮說,「看你的電影,就知道你是天蝎座。」雖然蔡明亮形容自己的星座是「最毒的那個」,雖然他說屬於冥王星的天蝎座是幽微陰暗的,雖然他總是拍社會底層、邊緣的生活,雖然有人看這樣的電影覺得不舒服,但在蔡明亮的電影裡,卻透出一種生命力和希望,還有一些不經意的幽默。
蔡明亮說,每個導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觀眾,而他只是拍真實生活的縮影,也更凸顯了許多生活中的荒謬。「很多人也許看我的電影覺得不舒服,我想,是因為害怕看到自己,雖然電影中我常常呈現出很不堪的生活狀態,但我『丟』了希望在裡面」,蔡明亮用手勢強化他的肯定語氣。
相對於在國際間奪下影展大獎,聲名鵠起,蔡明亮在國內的支持力量多半來自少數熱愛電影人士,而票房通常不盡理想,在爭取國片輔導金的過程也多所周折。談到這個結構性問題時,原本情緒開朗的蔡明亮顯得有些激動。
「很多罵我的人,是從不看我電影的。在和新聞局開會時,也曾有相關官員舉手說,蔡導演,我們都看不懂你的電影,或是『不要發輔導金給他,他專拍同性戀和給外國人看的電影』。我知道在我電影裡出現的場景,絕不是那種官方喜歡的、美美的畫面,我從不刻意避談這些問題,甚至我喜歡到每一個城市去看她最亂七八糟的地方,才覺得能看到更多的真實。有一次一位官員說,台灣不只是有這些髒髒亂亂的地方,還有很多漂亮的好地方,我說,『我留給你拍』。」
蔡明亮覺得,明明就有一大群人生活在物質條件敗壞的環境下,但往往乾淨的、秩序的社會忽略了他們的聲音,兩邊都無法和對方溝通。特別是在屢次獲得國際認同後回到台灣,總讓蔡明亮感到挫折和深深的寂寞。
他強烈質疑目前用票房來衡量電影價值的二分法。「我不反對以好萊塢『總動員式』的手法包裝造勢,但希望也能給執著於創作、風格鮮明的小成本精緻電影多一點的發揮空間。」他說。
⊙黃蕾採訪、孔繁毅攝影 摘自[ 美麗佳人 ] 199812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lovechang 的 bbs 電影板精華區
Copyright © 昔影.惜文. Template created by Volverene from Templates Block | Blogger Templates | Best Credit Card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