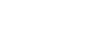小津論安二郎
發信人: degennes@kkcity.com.tw (), 看板: movie
標 題: [考古] 小津論安二郎
發信站: KKCITY (Tue Dec 28 11:44:32 2004)
去年是小津冥誕一百週年紀念,世界各地都有他的完整電影展不過由於寫的太慢,現在只能慶祝他誕生一百零一年了。這裡是一些小津自己,或是其他人提到小津,我選擇了我覺得有趣的部分,大多來自一些書,訪談,和其他電影。
另外,還有三篇更臭更長的文章『我們的藍調——小津安二郎』若要在BBS介面刊出,實在是會斷行斷到瘋掉,也為了節省網路資源,所以,如果對小津有興趣的朋友請到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degennes/
來交流指教,謝謝
大概沒有人比小津自己還來的瞭解他了,因為他是一個這麼忠於自己的創作者。
這裡應視為本文『我們的藍調——小津安二郎』的前言和長註,主要的資料來源是唐納瑞奇(Donald Richie)的書『小津安二郎的電影美學』(Ozu),台灣電影文化協會出的文集『尋找小津』,導演篠田正浩(『心中天網島』的導演,也是岩下志麻的先生)的短暫回憶演講,還有就是三十三部電影的觀後感(『小早川家之秋』沒來波士頓。而經天人交戰後,我決定去『爵士樂活化石』Sonny Rollins 的演奏會,而捨『淑女忘了什麼』和『獨生子』)。
之後的文章,我提出了一些我的看法,但絕對沒有批評唐納瑞奇的意思。事實上,在他之前,Paul Schrader(Martin Scorsese的長期合作編劇)就有一本書『Transcendental Style in Film:Ozu, Bresson, Dreyer』,但是那本書畢竟還是一個以西方人的觀點來看小津,一直到唐納瑞奇,才有比較客觀完整的論述。至於指出侯孝賢和聞天祥的小錯誤,只是因為他們是有影響力的人,弄錯總是不好。
關於小津,還真是像一千零一夜一樣,怎麼說都說不完。由於已經寫了太多,所以關於剪接,演員(尤其是岡田嘉子和司葉子),許多影片的有趣母題和細節都沒有提到,這是唯一小小的遺憾。或許,等到慶祝小津誕生兩百年時,我們在來說仔細一點吧。
關於唐納瑞奇的另一面,見『歷史敲門』於: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russiablue/
想知道小津的墓碑除了『無』字之外,還有什麼的,請見: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tarahuang
關於一些小津演員的介紹: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g1696838
小津的官方網站:
http://www.ozuyasujiro.com/news.htm
另外,以下若是沒有特別說明,都是小津自己的言論。
關於小津的想法:
就我的生活模式來說,小事跟著流行走無所謂,大事就得遵循道德,而藝術只能遵循我自己的意思,所以無法接受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我也瞭解這不夠自然,但沒辦法,就是討厭。日常生活中也有這樣的事吧,很討厭某件事,也知道這種討厭不合理,雖然不合理,但是因為很討厭,所以勉強不了自己。就因為這樣,自己的個性才越明顯,而且絕不妥協。所以即使是不合理的事,我還是會去作。
每個導演的屬性,是與生俱來的,不容易改變,成瀨兄和我可能都是屬於低音部,黑澤兄和澀谷實兄則屬於高音部,而溝口兄表面作風像低音部,但實際作風卻是高音部。大家各有各的調子。
1932年岸松雄曾拜訪小津家中,回憶道:『我推開一扇古色古香的門,映眼而入的,是一隻在籠子裡啼叫的鳥,記得那是一隻鶯。不一會,小津出現在玄關,一身怪異的打扮,穿了一襲皺白紋和服,上披了一件漁夫模樣的長掛,淺黃色的質地上,染了紅色的捕魚圖案。
穿過了長長的走廊,上了二樓他的書房。書房很小,只有六個榻榻米大,中間擺著腳爐,書冊凌亂成堆,畫筆畫具散的一地都是。小津從小就喜歡水彩,尤其是三宅克己的水彩畫。雖然沒受過正式的訓練,但是他都一直自己畫分鏡。
他的書桌上擺了一展精緻的小檯燈,書架上有成排的威士忌的酒瓶。櫃子上還放著耀眼的金色獅子頭,和一台留聲機。我問他可不可以放點音樂,他放了他最喜歡的(舒曼的)『幻想曲』。』
性格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簡單的說,就是人的況味。如果你不能傳達人的況味,你的工作等於白搭。這是一切藝術的目的。在一部電影中,有情感而無人的況味,是一種缺陷,一個能把表情百分之百做出來的人,未必能把人的況味表現出來,我們甚至可以說,表情往往是表現人的況味的障礙。它必須要被壓制,如何去壓制表情,如何從此一壓制中表現出人的況味,乃是導演的職責所在。
年輕的時候開始爬山,爬到某一個高度的時候,才發現另有一途徑,於是又往下改走此一新的途徑,這種人是大器晚成型的。我一直走同一條路,而當我快到山頂的時候,我也常想若從其它的路再爬一次不知道會怎樣,只是,現在的我,已經無法再重新爬一次了。
小津偶爾也挺好商量的,拍『東京暮色』時,在正式開拍一個斟酒的畫面之前,小津靠近中村伸郎的耳際,小聲的對他說說:『把瓶子轉過來,讓商標朝外。』因為Suntory威士忌酒場定期贈送小津大量的威士忌。
野田高梧女兒玲子的日記中,有一段是記載『小早川家之秋』的寫作期間,東寶的製作人打電話詢問工作進展如何的文字:『今天吃早飯時,藤本女士來電話,我們告訴她沒什麼問題,要是她看到他們放著工作不作,成天盡喝酒的情景,準會急跳腳。』
關於小津的編劇:
除非你知道那個角色將由誰來扮演,否則寫劇本是不可能的,正如同一個畫家。不知道他將使用什麼顏色,而無法動筆的情形一樣。對於明星,我一向不敢興趣,演員的性格才是最重要的,這不是他有多好的問題,而是他實際上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所投射的,不是劇中人物,而是他自己。
導演和編劇共事時,兩人必須要有某些共同的生活習慣,否則,工作一定難有進展。野田(高悟)和我,不管是熬夜,喝酒,或是其他的事與我都是同好,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我和野田一起寫劇本的時候,甚至對白中的片語隻字,我們的想法也都是一致的。有關道具或服裝的細節,雖然我們從不討論,但他心中的想法也總是與我的相符合。我們的想法從沒衝突過,甚至連一句話該以『嗎』或『哪』來結束,我們的看法也都是一致的。當然意見稍有出入也是免不了的,由於我們兩個人都這麼固執,想要妥協真是談何容易阿。
野田在小津死後回憶道:『如果意見相左,我們有時候會一連兩三天不交談,要嗎也只說些像是『唔,白樺樹總算開始掉葉子啦』或是『昨夜山谷裡有鳥叫』之類的話。如此過了幾天,說也奇怪,總會有和我們之前完全不同的想法,自我或他身上出現,然後工作就會再度順利的進行下去。』
關於小津的拍片:
決定小津攝影機位址的,是小津對於一種具有繪畫上平衡感的構圖之要求,這種要求使小津的攝影機拉的低低的,而且幾乎與場面保持垂直的角度。厚田春雄記得小津對他說:『厚田阿,日本房子的構圖有其難處,尤其是角落的部分,想處理的像繪畫那麼嚴謹,實在很難,補救的辦法就是低角度攝影』
下河原友雄在一次座談會時說:『東寶有一個攝影師,叫秦大三,曾為『宗方姊妹』和『小早川家之秋』拍過劇照。有一次交談的時候問我,會不會覺得小津的構圖和昭和初期攝影比賽的得獎作品很像。他說小津在那個時候就很迷攝影,那種風景和靜物的構圖一直沿序到後來。像酒店的大酒桶斜斜的靠在一起之類的構圖。』
下河原友雄後來繼續說小津買了一台萊卡相機,不斷的拍照,自己洗照片,還送去參展。
拍攝『東京暮色』中,當小津移動桌上東西時,篠田正浩(當時副導)吃驚的告訴他,這樣會在連續上造成嚴重的破綻。小津停下來,看了看他說:『連續?喔,原來你指的是那個阿。你錯了,沒有人會注意到那種事的。而且,這麼變一下,構圖比較好看。』
笠智眾回憶說:『我必須承認,我只是小津用來作畫的原料…今天想拋開他來談我自己是不可能的。我曾經聽小津說,『笠不是一個純熟的演員,這就是我喜歡用他的原因』這話一點都不假。』
小津心目中的理想演出是:『『小狐』中貝蒂戴維斯站在垂死的丈夫身邊倒茶的場面。她沒有作任何表情,平靜的把茶倒到杯子裡面,整個場面只有杯子清脆的觸擊聲。』還有『看看『俠骨柔情』中的亨利方達:一動也不動,毫無表情—這正是福特的過人之處。方達雙腿擱在柱子坐在椅子上,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方達和福特的默契實在令人羨慕。』
關於小津的電影:
這個故事(『早安』)在我心中擺很久了,真要拍它,並沒有這麼容易。有一次,我在導演協會的會議上,把這個故事敘述了一次,大家都說很有意思。於是我說,誰有興趣,我就讓給誰拍,但沒有半個人表示意見。我只好抱著故且一試的心態,自己把它拍出來。
我原先所想的故事,比較低調。後來隨著年歲的增長我考慮了票房的因素,因次,就試著儘可能拍成一部逗趣的片子。我說的票房因素,其實說是為了想讓更多人看到它,或許更貼切。而且,我才剛得了藝術院的獎,我可不願意人家說,現在我專拍嚴肅的片子。
就主題而言,這(『浮草』)是一個舊時代的故事。他發生的時間,雖然是現代,但是氣氛是屬於明治時代的。不過,如果真的把時間挪了回去,又免不了有考證上的麻煩最後,它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利用現代的時空,表現一個舊時代的故事。
另於日記中:
惜酒不肯飲,佳作安得出?觴來為之盡,酒深文亦奇『浮草』之為佳作殆非僥倖,只要看看廚房中成排的空酒瓶,便知其然
關於『秋日和』,小津說:『有時候,明明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人們偏要把它搞得很複雜。感覺上,人生雖然複雜,但是說不定,它的本質就極為單純。這就是我在這部片子想要表現的。
利用情感來表現戲劇,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你可以用眼淚,用笑聲,把悲哀和歡樂的感受傳達給觀眾。但是,你同樣可以摒棄所有戲劇性的技法,完全不假手哭泣,而仍能顯示悲傷,完全不假手戲劇的跌宕,而仍讓人感認到人生。
在這部片子裡,我試圖完全以這種方式來演出。自『戶田家兄妹』起,我一直都希望能做到這一點。不過,這相當難,這部片子表現得還算差強人意,但仍距理想甚遠』
篠田正浩回憶:拍完『東京暮色』後,小津要他去買一些下酒的小菜來慶祝一番,他買了一些當地著名的豆腐回來。小津吃到一半,突然對他說:『你知道我總是說我是個作豆腐的,但是這一次是完全失敗的豆腐。』
之後在『彼岸花』的座談上,岩崎說:『所以說『東京暮色』就是因為小津先生想要站在年輕人的立場,描繪年輕人的故事才會失敗的吧?』小津自己說:『不,不可混為一談。『東京暮色』主要是描述笠智眾因為妻子和別人私奔,所以獨自撫養兩個小孩的故事。更令人難受的是妻子竟然和自己的屬下私奔。
多年以後再聽到妻子的消息時,心情已平靜無波徹底冷靜,我想描繪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但是一般人狠少從這一點理解這部片,只注意到劇情的高潮起伏。所以當劇中母親在出現時,因劇情起伏一般觀眾跟著驚喜,其實那只是為了劇情張力所做的處理,就一般的心裡來說,這種情況下,父親是不會震驚的。總之,這種東西很難捕捉。』
其他:
篠田正浩半開玩笑的說,小津當初發現岩下時,非常的高興,說她是十年才出一個的氣質演員,一直誇他很美。但是我後來(把她娶回家後)才知道,她在電影所有的美麗,全部都是小津的功勞。
外國人看電影總是一味的注重故事,至若『早春』中上班人的生活,無常,以及故事之外的氣氛,他們更本不懂。不懂,所以就動不動說那是禪。
小津對於『我們要愛母親』映象很深,『並非它拍的好,而是因為在拍這部電影時,家父過世了』小津的父親,小津寅之助是死於狹心症,死前小津在他身旁,野田回憶小津對他說:『父親轉過頭來看我,用手撫著我的膝蓋,彷彿知道我就是他最後能託付的人,當下我熱淚奪眶而出』(這和『父親在世時』的最後一場戲,極為相似)之後,小津便一直和他母親住在一起。
在伊丹十三的電影『稅務員之女第二集』裡面,查逃漏稅時,有一個空頭宗教組織,那個登記成立的人,是小津的照片,他們也找到當初登記的人,客串演出的是笠智眾。
日劇『我和她和她的生存之道』是一個關於家庭的故事,鏡頭只在每集接近最後動一次或兩次,顯然導演平野真也是個小津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