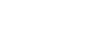發信人: shihlun.bbs@bbs.cs.nccu.edu.tw (渡輪地專欄), 看板: movies
標 題: [City Guide]蔡明亮:這個時代缺乏的是天真與熱情
發信站: 政大貓空行館 (Sat Nov 7 23:30:53 1998)
出身於馬來西亞的蔡明亮,卻定居在台北;而他對台北人的觀察,從《青少年哪吒》、《愛情萬歲》、《河流》到新片《洞》,既敏銳又貼近得令人不敢相信。
他代表亞洲地區,以世紀末為主題的電影拍攝了《洞》,在這部電影中,究竟世紀末的台北都市,呈現在蔡明亮心中是什麼樣的樣貌?以下是我們的採訪
Q:《洞》片中安排了罹患世紀末傳染病的某些徵狀,似乎跟現代人的冷漠特質似乎有點像?
A:我覺得這部電影是很象徵性的,所有東西都很象徵,暗示著它可能會發生。我認為現在的人,尤其是住在台北的人,都不太有尊嚴,跟有錢這個事實沒有成正比。
所以我寫的未來時代,是一個很壞的時代。世紀末台北的傳染病流行,有錢人應付壞時代太容易了,走就對了;而沒錢的人即使離開這棟大樓,還是得住在台北裡,這群人是最可憐的一群。我把角度放在窮人身上,看他們怎麼應付這樣壞的未來時代。
我們的社會是看來大家好像都很有錢,可是沒有人教你怎麼用這個錢,物慾的追求,看起來好像生活改善了,但實際上反而變得更壞,精神上面是空虛的,我指的是文化的部份。
Q:所以世紀末的台北是不停地下雨?散播傳染病?
A:你說下雨是天災,有可能是我們造成的。我們的氣候改變,也有可能是我們破壞了環境,會有傳染病,可能50年前就存在了,只是因為我們改變了某個引發他們的因素。
Q:電影中的傳染病會讓人變成蟑螂?這樣的構想是哪裡來的?
A:我覺得人最厲害的地方是在適應這樣的環境,而不是改變這樣的環境,在任何壞的環境都能生活。
人變成蟑螂,表面上看起來是病,實際上是在調整自己適應,但是,變成蟑螂就沒有尊嚴了。可是,他又不由自主地要變成蟑螂,最後我沒有讓你們看結果到底怎麼了,因為我也不知道。
所以最後一切都是從頭開始,最終楊貴媚就出現了,一切好像一場夢一樣。但是傳染病又無從救起,所以李康生就哭了,這杯水的意思,代表一切重頭的意思。李康生以前只是偷窺他,但經過這樣的災難後,願意給他一杯水,甚至是一隻手。
Q:為何在電影裡大量使用歌舞片段?
A:這些早期歌舞的用法,看起來是要與現實(戲中)做一個對抗。現代的人比較冷漠,而未來的時代可能比較敗壞,什麼東西可以對抗它?我覺得這樣的東西可以對抗它?
我覺得這樣的東西可以對抗—天真、熱情、浪漫、敢愛敢恨的個性,是現在這個時代比較缺乏的,這種東西放在冷酷的現實裡,我認為有對抗的意味在。我用了五首歌,每一首歌用一用,又回到現實,其實好像打仗,我用這樣的處理方式。
Q:《洞》裡的歌舞片段,全是60年代葛蘭的歌曲,導演為何對這位明星情有獨鍾?
A:我喜歡老歌,尤其是30年代的上海時期到70年代香港時期,小時候就是聽這些歌長大的,我感覺那時的歌旋律都很甜美、純真,即使是再熱情的歌,感覺都是優雅的,有一種歌舞昇平的感覺。
現在的新加坡,馬來西亞音樂城中還有很多賣老歌的專櫃,台灣則比較不流行。
葛蘭在50、60年代很紅,她的特色是能演又能唱,每部電影中都得唱歌和跳舞,還要發明新的舞步,是歌星也是演員。比如電影《曼波女郎》裡的曼波舞,歌曲「我要你的愛」、「胭脂虎」、「我要飛上青天」等等,即使直接、熱情都顯得優雅,她的歌和電影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一種氣氛。
為什麼要放在我的電影中是因為我喜歡她。用她的歌,另一個理由是因為現代的歌比較沒有個性。葛蘭的時代,我覺得還有一些個性。以前的歌星真材實料,樂隊的氣氛很飽和,而現在的歌,太靠技術,從創作到製作過程如同機械般製造出來,他們要的是偶像,臉孔反而比較重要。
Q:這些歌舞片段也有幫助劇情推衍的功能?
A:多少有一點,但我的歌舞用法很特殊,不太像好萊塢的用法。
好萊塢的歌舞在攝影棚中製造,假的東西,做出富麗堂皇的背景;而我拍的時候,是用現實的背景,把一個舊的東西放在現在,現實裡又有一點夢幻,有另一種氣氛。
Q:請談談從你早期的電影 《青少年哪吒》、《愛情萬歲》、《河流》到《洞》的轉變?
A:每一次拍片當然都希望跟前一部不一樣,但電影中的大環境都一樣,都在看住台北的人, 只是希望每次的角度不同。
比如《海角天涯》、《青少年哪吒》那個年代,是從人與環境的關係,來看這個時代的問題。
而後《愛情萬歲》則從人的行為,做的工作,與人的交往,來看她的內心活動缺少了什麼。到了《河流》,我就想看人內心黑暗的那一部份,對某些人來說,如苗天飾演的同性戀父親,是很陰暗的。
到了《洞》則是拍另外一個角度,人與環境的戰爭,《洞》比較特殊的一點是拍一個還沒有發生的事。
Q:聽說你很喜歡楚浮?現在還是嗎?
A:對啊,我喜歡的東西都不太容易改變,其實60到70年代大部分的歐洲電影我都很喜歡,因為我覺得那個時代彷彿是一個電影時代的高峰,各種形式、內容都被拍掉了,是一個非常創作自由的時代。我會特別喜歡他,是因為他是我第一個接觸到的導演,我喜歡他的電影像《四百擊》、《日以作夜》。
Q:你怎麼知道自己會當導演?你覺得當導演的條件是?
A:我也不知道,命運的安排吧,這沒有一定的道理。沒人教我寫劇本,我的方式是自己想出來的,因為要面對工作,沒有人能定一個標準出來。 我的方法是過平常的日子,我想是與你生活的過程有關,從生活的感受裡想到一個題材,比如說我對外籍勞工感興趣,,我就會去找他們聊天,了解他們。我的創作部份是蠻自然的,當事情碰到我,我想拍那個東西,那就是了。
Q:最近有看電影嗎?
A: 看了《花木蘭》,還蠻好看的。其實我看很多老片,常到重慶南路買老電影的錄影帶,放在家裡,慢慢看。最近還看了《豔陽天》,大衛連拍的,一部美國的文藝片,背景在威尼斯,也很特別。
記者/ 陳蓓蕾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lovechang 的 bbs 電影板精華區
Copyright © 昔影.惜文. Template created by Volverene from Templates Block | Blogger Templates | Best Credit Card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