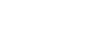也談小津(舒國治)
發信人: sahala1011.bbs@ptt.cc 看板: movie
標 題: [人間]也談小津(舒國治)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 (Sat Nov 15 16:15:31 2003)
在萬隆的一家餃子店吃了十多年水餃,味道很好。但這家店的酸辣湯與玉米湯我從來沒點過。十多年來,我想老闆娘一定覺得奇怪,當然她也沒問過我。若她問我,我會怎麼回答呢?
我常麻煩她給我一碗餃子湯,當然嘛,「原湯化原食」;另就是,我更傾向於喜歡自然形成的湯,如餃子湯,而不喜歡硬做出來的湯,如酸辣湯、玉米湯。
就像便利商店賣的幾十種鋁箔包的飲料,幾乎一樣也沒喝過,一樣也不曾注意過,它們被我稱為「編製過的水」,而不是我平時喝的「自然形成的水」。
小津安二郎藝術之登峰造極,論之者多矣,我亦最拜服,雖我懂曉他饒是淺薄。他的電影,便是我所謂「自然結成的劇情」。不同於大多數電影是「編出來的劇情」。小津的這杯水,不同於眾多花樣繽紛的飲料,它滋味更雋永。
正為了達到「自然結成」,小津絕不用電影手法去妄自改動真實。譬似他絕不用倒敘鏡頭。倘說及往事,能用口說的,便主人翁口說即是,絕不攝一畫面嵌入。譬如取出一張相片介紹對象,多半不拍那相片,非必要也。又既然前述相片未被攝下,則其後女主人翁偷偷瞧一眼真實對象,此對象亦不攝取。此言《麥秋》一片之例也。
又「自然結成」是如此不易,小津連攝影機也不輕移動。攝影機不動,則人物必須移動;人物先在廚房,一走走到主廳,則攝影機早在主廳恭候,拍入。人物問知爸爸在樓上,便轉身登樓,下一鏡頭攝影機亦早在樓上相待人物自梯口現身。
西方電影的橫向搖攝或自下登上的昇攝,小津絕不取。一來西洋電影陳腔慣使的攝影陋習不免來自商業娛樂片輕浮傳統,尤以導演不知如何面對當下劇情時便隨興驅動影機,二來小津素知日本家屋緊促空間與人物緊密相繫關係,原本惟有此法方能恰如其份的呈現真實。
藉由平淡的片段串聯影片
小津在攝取人物對話上,亦做到形式完美。兩人對話,甲說一些事,乙說「是嗎」;甲再述說,乙說「這樣啊」;甲接著說,乙又說「是嗎」……如此,鏡頭先甲後乙,甲長些乙短些,韻律有致,三五句交話後,韻律又推往另一拍子,令之稍有變化,教人自然專注以看,且看得十分舒服。
他不愧是將平日事拍得完美之至的「片段篤寫」之巨匠,而他的整部片子亦全由如此精緻的平淡片段所構成。
因皆是平常事所結成的情節,小津影片的起名,常顯得很相似;如《早春》、《晚春》、《麥秋》、《秋日和》等只如是時光變移之字眼,教人抓不住確意。要不便是一些如《浮草》、《彼岸花》、《東京暮色》、《綠茶飯之味》、《秋刀魚之味》這類很飄忽的寫意的名字。
有人會說,這教人記不住哪部片說的是哪件故事。是的,或許正是如此,小津正是不希望大家把特定的哪部片很特定的記住,一部一部往下看便好了,每一部皆將它視為「無題」亦可。事實上,在觀者的依稀印象裡,這一部與那一部穿插連接在一道亦像是言之成理。
且看他的人物,多姓平山。這個平山,若年歲大一點,便由笠智眾(《東京物語》、《秋刀魚之味》)飾演;那個平山,年歲稍輕呢,就由北龍二(《秋日和》)或佐分利信(《彼岸花》)飾演罷了。
甚至家中的小孩,大的總是叫實,小的總是叫勇(《麥秋》與《東京物語》)。
甚至,這些不同的片子,其主人公吃酒的小店,常是相同的「若松」。
他們生活在相當侷小卻安定穩篤的空間,五倫極是和睦;父母與子女,公司中的同事,中年團聚的中學同學,出遠門訪探親人……等等,這是小津最深情凝視的人生。而此人生他用很拘限的場景來呈現,且說幾種:
一、進玄關,脫鞋,進主廳,男主人翁脫下西裝,丟下手帕,俱落在榻榻米上,女主人翁隨即收拾折疊。
二、辦公室,總是那樣窄窄長長的。有訪客,則很有禮儀的對話。進室前,或敲門或有人領進。
三、小酒館,人倒酒、喝酒極是輕巧熟稔,彷彿很得品嘗此中深味似的。又挾菜吃菜很小口,如有節制。而凡拍酒館,先出一個空鏡頭,呈現招牌及窄窄的弄堂。
四、換景而用的空鏡頭,常有小孩上學的畫面。
一部又一部的精緻作品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恰因東京影展之便,參觀了小津的九十歲紀念展。其中展出了小津的Pique帽子,這種日本導演(甚至不少日本民眾)原就喜戴的款式帽子,竟然最後成了小津的招牌。今日我們若提說「小津戴的那種帽子」,相信人人知道指的是什麼。
小津頗好相撲,有一幀照片攝於他在蒲田攝影所,與同事合影,大約那是他年輕時玩得最無憂無慮的一段時光。
他體格高大,或許遺傳自母親。小津一生沒結婚,最後二十多年與母親同住在北鎌倉,母親塊頭大,八十多歲時,因家住坡上,便很少出門,為了不願返家時爬坡困難。又她即使生病或太累,也不願讓人揹,主要因「楢山節考」之傳說謂揹老母乃欲棄葬之云云。
小津有在筆記本上繪草圖的習慣。中日戰爭,他亦到了中國,一九三九年四月的日記將修水河渡河戰也繪成地圖,可見的地名有:龍津市、堰頭劉庄、尖山、永修等。
他喜歡的餐館,也記在筆記本裡,並且繪上地圖,如人形町的「四季?里」,澀谷神宮通的「二葉亭」、江戶路一,四的「泰明軒」。另外,他也讀小島政次郎的飲食書。
小津好酒,常有與野田高梧合寫劇本幾十天後,點數飲空的酒瓶共計幾十或上百的趣談。他片中人物亦偶一醉。此他人生頗為自約後偶求釋脫之舉。他年少時由於父親遠在東京經商,他在鄉下只受母親照料,頗得自由調皮之樂,及受學校趕出宿舍,更因通學之便飽看了當時好萊塢的默片。
小津固然思想開放,行動自由,言語諧趣,但其心底深處依稀有一襲謹約幽寂的牽引,致他終於不得不逐漸成形出今日一部又一部如此精密的作品。小津,他像是全生命融入的藝術家,所有的童年,所有的生活歷練,所有的吃飯、談天,所有的與人相接,所有的觀看市井,皆像是最後沒有了他自己,皆像是全數為了藝術。
他死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距他生的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恰好是整整一甲子,一天不多一天不少,風格何其精密嚴謹也。曾有外傳他與女演員原節子計畫結婚之說,但內向含蓄的小津,始終不曾言及戀愛或結婚之事。小津死後,原節子從此不再接戲,像是矢志以她的演員事業與小津的離世一起成為過去。
(本文作者舒國治,作家,喜歡遊蕩,作品以散文為主,著有《讀金庸偶得》、《理想的下午茶》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