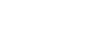闡揚東方生活藝術的哲人─小津安二郎
發信人: aa541.bbs@ptt.cc (優皮五), 看板: movie
標 題: [小電影主義]闡揚東方生活藝術的哲人─小津安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 (Fri Dec 5 18:49:18 2003)
非同步影評】
闡揚東方生活藝術的哲人──小津安二郎 文‧張昌彥
與小津安二郎結緣,始於一九七一年。那時,我剛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演劇研究室專攻電影課程不久,在一位同修「電影特論」的同學帶領下,第一次觀賞了小津的作品。那部《東京物語》(1953)深深感動了離家在日本求學的我,也讓我真正的體會到 父母親對子女的包容與愛情;
尤其片中兩老準備上東京整理行囊找空氣枕頭的場面,在我腦海中立刻浮現家鄉父母平日的互動行徑,不禁讚歎小津的細緻和捕捉生活的準確性,也因此成了「小津迷」。而後,更多次搜尋觀賞和研究他作品的機會(當時錄影帶還很少),也為此走遍東京的許多二輪電影院。
一九七六年一月,日本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電影中心,以兩個月的期間做小津作品專輯上映,將小津現存作品三十五部半(亦即本次上映之片目)全數放映,這也是我首次完整的看完他的作品,卻也因此更醉心於他的電影。
而自己對小津之癡迷也成了研究所人所共知的事實,以致日後東京的「電影藝術出版社」委託早大演劇研究室書寫「閱讀小津安二郎」一書時,我也幸運受邀參與寫作。而且,在我離開日本以前,同是「小津迷」的好友貴田先生更陪我找到鎌倉圓覺寺墓園,帶了一小瓶白蘭地去祭拜小津一番(小津以嗜酒聞名),以示對他的崇仰。
*源自真實生命的影像情蘊
小津作品儘管在形式、技巧和藝術成就,在影壇上都具有獨特且崇高的地位,然而,他的作品卻沒有一般所謂「藝術片」的艱澀、沈悶和刻意。
我以為小津是一個真正的生活藝術家,他關心的不是冥想的哲理,也不是夢幻的虛擬世界,他是從生活中擷取經驗,再將經驗表現在其作品中,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充滿了小津式的情感思慮、生活形式、甚至處世的哲學,而這些東西也正是那個時代的日本人(其實更是東方人)之共相。
小津的電影隨著他自身的人生成長步履,做漸進式的改變,其作品中的主人翁,更是隨著小津年歲之增長、社會地位的迭升,做出同等的變化,從他早期的大學生對考試的憂心《我落第了,但……》(1930),或對宿舍搬遷的煩憂《開心的走吧》(1930),或是大學畢業生尋找職業的困惑《我畢業了,但……》(1929)等等。
到初入社會低層薪水階級的掙紮《我出生了,但……》(1932)、《獨生子》(1936),延伸到步入前中年的白領階級,為家族幸福付出的努力《父親在世時》(1942)、《風中的母雞》(1948)、《晚春》(1949)、《麥秋》(1951)、《東京物語》(1953)等的家族主義的回歸。
進一步也開始觸及生老病死的思考,以致後期中老年人對子女之婚姻煩心,這時主人翁幾乎都是公司的上層幹部《彼岸花》(1958)、《秋日和》(1960)、《 秋刀魚之味》(1962)等等;這些生活及議題,事實上也是我們人生中必經的階段和過程。
小津作品中的素材,恆常是東方人關心的家族、師生、朋友間的人際關係,在男女的私情上卻較少觸及,這或許是源於東方社會較少在人前公然討論男女私情的習性,亦或許是誠實的藝術家小津自身生活的寫照(小津一生未婚,且終身與母一起生活)。
而其作品的議題也均圍繞著求職、結婚以及生、老、病、死等每個人生中都不可倖免的問題做省思,難得的是他在處理這些通俗性的素材和議題時,竟能規避一般通俗戲劇刻意製造聳動的衝突或謾罵爭吵,甚至拳打腳踢的窠臼,他只是輕描淡寫的勾勒出那些生活在廿世紀中葉的日本人(或說東方人)的真實樣貌。
在那個時代裡,家族間的不快或隔閡,在傳統倫理的規制下,只有讓忍耐或諒解和時間來解決。這就是東方社會迥異於西方生活的所在,也是東方謙讓文化異於西方掠奪思潮的相異處。小津將這樣的人品舉止,描繪得栩栩如生,使觀者感受到這些人物宛如你我身邊的親友或父祖。
小津的作品經常被稱為「小市民電影」,然而他的「小市民」(庶民)並非是販夫走卒的小市民,而是更具普羅性的薪水階級,因此他的人物不可諱言的,是較偏向於智識份子的族群,或對生活有所省思的人,而且,他們大部分都個性溫和,念舊情且服膺倫理,常為別人著想,更是努力於工作的老實人,以笠智眾、原節子扮演的角色為代表。
然而他們也並不是一味的道貌岸然或零缺陷,有時他們也會執著得有些固執,猶如《麥秋》(1951)中之紀子(原節子),有時也會嗜酒,喝到微醺(如許多作品中之笠智眾),但他們卻能有所自製,不致造成僵局或酒後亂性,這是大部分守法的日本人之縮影。
在小津電影中的父親,不像同樣是受儒家思想洗禮的中國父親的權威和霸道,(唯一的例外是1958年《彼岸花》的佐分利信)他們都能為子女著想,他們忍耐自己的支配慾,以無奈的包容態度來面對子女,甚至以幽默的形式來接納事實,像《東京物語》中的笠智眾和十朱久雄(服部)。
談到幽默,這又是小津作品中的另一個特色。小津對引導孩童入戲有其獨到之處。小孩的天真、善模仿都是小津創造喜感的源頭,《我出生了,但……》中,斑馬的推論,以及獅王牙刷毛髮之爭執;或上將中將的定位,幽默中不失兒童的純真本性;在《早安》(1959 )中,小小孩對大小孩的模仿更是令觀者產生笑點的原動力。
事實上,小津的幽默不僅呈現於童輩之間,中年人優雅且具暗示性的鹹濕笑話也讓觀者發出會心的微笑,例如《彼岸花》和《秋日和》中幾個中年舊友在料理屋「若松」尋老闆娘(高橋豐)開心,極為有趣,且樂而不淫。
從這場景中觀眾可以得知這群不良中年,在年輕時候彼此戲謔的真情誼,這種對過往事實的描繪,能以這麼簡潔手法交待,達到令人深入理解的處理,相信無人能出其右。這也是我看過眾多的電影中,描繪中年人友誼最深刻的作品。
*恬淡自然的豆腐之味
記得在某本書上記載,今村昌平在年輕時當完小津的助導後說:「小津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植物人」,其意在指責小津之人物都太溫文儒雅,欠缺活力,當然這是因為今村和小津是兩種完全不同典型的人,因此會產生對電影藝術理念的差異,這是無可厚非的。
正如小津自己曾說:「我是做豆腐的,所以你要我做炸豬排是辦不到的」(「小津安二郎—人?仕事」,蠻友社,241頁,1972)。同樣的,也有人非難小津與社會脫節,說他將自己束之高閣。
我以為持這種論調者,對小津作品的閱讀太過表面化,因而造成這種負面的看法。首先,小津根本無意拍攝社會問題劇,因此,在他作品中,不可能突顯社會問題,他只是將社會問題淡化,將其視作社會現象而融入戲劇中。例如1929年的《我畢業了,但……》,它以社會不景氣業困難的社會現象來作為戲劇之背景。
而《我出生了,但……》也反映出東京居不易,因此主角搬到郊區去。《東京物語》則觸及戰爭未亡人戰後的生活以及勞動組合(工會)制度的建立。
更明顯的就是在《早安》中,我們看到千篇一律的公寓式建築的出現,也呈現出父母醉心於要小孩補英文,而小孩則期待買電視以及六○年代日本全面電氣化開始的社會現象;甚至更入探討到退休制度,及對尚有精力之初老年者的威脅和失落;這樣樣都在敘說著社會的變遷。
「寫實」可說是小津電影的基調。不論從素材、人物、事件來看,它都徹底的摒除虛構性的設計。而更令人驚奇的是小津電影的節奏,竟然也是進行於自然生活之韻律中。
小津在處理人物時,從不輕易的放過任何一個有效的舉止或眼神,因為從這些舉止或眼神中,常會醞釀出人類的心思和情感。例如在《東京物語》中,大姊(杉村春子)打電話給紀子(原節子),請她帶兩老去市區觀光。杉村一邊講電話,一邊轉動著紙扇,以掩飾她的心虛。
這種不厭其煩的交待,對習慣於好萊塢故事主義的觀眾而言,也許會覺得冗長,但對於關心「人」的觀眾,那看似無意義的畫面,其實是可以更豐富劇中角色的內涵。
小津非但在這種直接發生作用的場景上做生活節奏的捕捉,就是在轉場時,往往也會將鏡頭停留幾秒鐘再換場,其目的除了帶給觀眾反芻加強深刻的印象,同時,它往往也是劇中人從一個場所走到另一個場所的時間節奏計算;更是帶給觀眾心理上的準備。
這是小津極獨特的手法,也正是小津自己一再強調他想捕捉人類生活中自然的節奏,因為他認為那是最美的。
傳奇性的小津安二郎,生於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並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即「還曆」(六十歲生日)當日過世,他一生拍過五十三部劇情片及一部紀錄片《菊五郎之鏡獅子》(1935),其中無聲片佔了三十二部。
而且,在他樹立風格之《我出生了,但……》(1932)前,他曾做多方的嚐試,尤其以模仿美國片形式之作極多,《那夜的妻子》(1930)及《非常線的女人》(1933)就是最好的見證。
由於關東大地震(1923)時 ,將小津前期之作品燒毀殆盡,目前剩下之作品只有三十五部半,其中《突貫小僧》(1929)殘缺不全。幸運的是中、後期精采的作品都存留下來,我們才有機會窺視小津的藝術全貌。
特別是在後期作品中,我們在他對老人從孤寂、無奈到坦然地接受現實的描繪,雖然有些不忍;但對於能抱持這種超脫的人生觀的小津,我們不得不說他真是一個東方的生活藝術哲學家。
(原載於「尋找小津:一位映畫名匠的生命之旅」
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