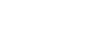發信人: jardin18@kkcity.com.tw (弱智浩二), 看板: movie
標 題: 李安.十年一覺電影夢 1 (轉貼自東森新聞報)
發信站: KKCITY (Tue Dec 3 01:54:00 2002)
舞台,改變了我的一生。在此,我的靈魂第一次獲得解放。渾沌飛揚的心,也找著了皈依。
一上舞台我就強烈的感覺到,這輩子就是舞台。清楚了,原來是這麼回事。它擦亮了我的雙眼,呼喚、吸納著我的精魄。我逐漸了解,所謂的升學主義、考大學,除了培訓基礎知識與紀律,對我毫無意義。遵循常規,我的一生可能庸庸碌碌;但學戲劇,走的可能就是條很不平常的路 .
但剛進藝專影劇科時,誰也沒當回事。有些人就是去讀一個月,然後辦理休學,準備重考。戲稱影劇科是第一○八志願的我,也打算重考,所以在我臉上找不到新鮮人的喜悅。當時學姊施秀芬(廣播主持人金笛)正編導一齣獨幕劇,還缺個男主角「詩人」,經同學推薦,選中我來演。
她覺得我雖沒有詩人的飄逸,但「面部表情」尚可,照他們的講法是,臉上掛著一副多愁善感的憂鬱氣質。這齣戲是個轉捩點,記得第一次站上舞台,強烈的聚光燈灑下來,面對燈光之後黑暗中的觀眾,我第一次感覺到命運的力量,是戲劇選擇了我,對它我無法抗拒。
接著又演出美國作家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名著《玻璃動物園》(The Glass Menageries)的男主角湯姆。從此在藝專,我一路擔任男主角,演戲不下十五齣,並在民國六十三年拿下大專話劇比賽的最佳男主角,同時自編自導獨幕劇,改編、導演外國劇本,興頭很大。
可能國內第一次實驗做圓形劇場即是《泰吉絲的故事》,該劇由友人余季編劇,我執導,我將觀眾席設在中間,四周劃為表演區。一搞戲劇,我什麼都想嘗試。
那時候學藝術,沒有很多大環境,不過藝專的環境很適合我,三專、五專、日夜間部齊聚一堂,總共才七百多人,自成一個小天地,有音樂、美術、舞蹈等七科,大家都是學藝術的,悠遊其中,我覺得很自在。
找到自己
到了藝專後,我才真正面對另一種人生的開始,原來人生不是千篇一律的讀書與升學,我從小到大所信守的方式並不是唯一,其實每天可以不一樣,我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很過癮。
可是爸爸看了很傷心,因為環境實在很差,我又是他最寵愛的兒子。那時藝專的校舍很簡陋,爸爸第一次送我到學校時,一看伙食及宿舍,難過得說不出話來。因為老鼠正沿著柱子跑上跑下,一間幾坪大的小房間裡擺了七個床位、兩張桌子……,聽說他回家後大哭了一頓。現在那些宿舍都改建成宏偉的校舍了。
第一個學期快唸完時,爸媽一起北上看我。那晚,北一女鄭璽璸校長請我們吃飯,席間鄭校長說﹕「小安休學吧,住到我家來,我請最好的老師給你補習,明年重考。」
飯後我們父子倆獨處時,爸爸問我﹕「要不要重考?」
我說﹕「我覺得我是屬於這方面的!」
爸爸決定支持我,他說:
「不要再重考了,不過我有個條件,畢業後出國。」
當時大家心情都很矛盾,我不忍心看爸媽難過,他們也認為我很不甘心,覺得我應該考上更好的學校。
但是我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充滿自信的喜悅,
不再六神無主的過日子。
藝專時期,除了在舞台上找到自我歸屬感外,
對電影也有了另一層的體會。
打從在娘胎起,我就和電影結緣。媽媽懷我時,最不能抗拒的兩個嗜好就是看電影及啃甘蔗。在我還不會走路時,她就推著嬰兒車帶我進電影院了。那個年代,電影是最佳娛樂。
從童年起到求學期間,我看了不少電影,每當心情低潮,電影院就成了我的避風港。看電影時,每逢感人之處我就會掉淚,所以經常是兩眼紅腫的走出戲院,可能這也影響我日後拍電影的品味及要求,希望能拍出感動人心的電影。
記得有一次跟媽媽去看電影,我好奇的問道﹕
「為什麼我們老看外國片?」
媽媽說﹕「外國片好看啊,等你長大,
看看能不能拍更好的國片。」
不過小時候看電影僅只是娛樂,也沒多想,更沒想到電影還能啟發其他的想像,直到進藝專後,我對電影的想法才有所改觀。
藝專時,看了本翻譯的《超級巨星》,才知道電影導演是超級巨星,對作者論慢慢有點認識。麥克.尼克斯(Mike Nichols)執導的《畢業生》(The Graduate)是我的啟蒙電影,一年級時看了這部描寫人生沒有遊戲規則的片子,第一次讓我有「觸電」的感覺,影片裡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不按牌理出牌的調調,以及電影中衝撞社會制約的主題,與我當時的心境有所共鳴。
《畢業生》是部六○年代末的電影,因主題「有違倫常」,到了七○年代初才在台灣上映,本來達斯汀.霍夫曼周旋於母女之間的情節也改了,母女成了姊妹。我連看三遍,感覺到電影不光是講故事,還表達些別的意涵,腦筋開始有點想頭了。
到美國後我又重看了幾遍,對《畢業生》還是喜歡,不過是另一種對社會諷刺劇的喜歡了,因為我對這個社會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永遠記得它當初帶給我那種觸電的感覺。
一年級下學期時,台北的大專院校間開始流行看藝術片,大家都到台北漢口街的台映試片間去看,每週一部。我看的第一部藝術片就是柏格曼(Ingmar Bergman)的《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帶給我極大的震撼,看完後我兀坐在試片間內,久久不得動彈,也不願出去,連看兩場。
第二部是狄西嘉(Vittorio de Sica)的《單車失竊記》(The Bicycle Thief),第三部是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慾海含羞花》(Eclipse)。藝術電影這頭三炮就轟得我幾乎久久不省人事。
當時台灣所有的藝術電影不如現今,十分有限,也沒有影帶、影碟,所以觀賞藝術電影的經驗非常珍貴。其他各學校有時也會舉辦電影欣賞會,我就一部一部的看。自柏格曼等人的電影裡得到的啟發與感動和《畢業生》又很不一樣,柏格曼讓我感覺到導演的存在,意識到藝術電影的力量。
超八釐米攝影機
那時在藝專,學校拍不起電影,只在畢業前讓所有技術組的同學扣一下十六釐米攝影機,我不是技術組的,一直沒碰過電影攝影機。二年級時,我看到有人在拍超八釐米影片,一個香港僑生說可以幫我從香港帶機器進來,我就跟父親要了錢去買。
這是除了書以外,父親送給我唯一跟電影有關的禮物,我把它當寶貝,用這台攝影機拍了一部十八分鐘的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懶散》,靈感來自余光中的短篇小說〈焚鶴人〉,內容敘述一位畫家寫生時看到白鷺鷥在天空自在的飛翔,就想做一隻如鷺鷥的風箏,結果風箏飛了幾次,都飛不起來。
在這部劇情默片裡,我想表達藝術家面臨理想與現實落差的挫折與掙扎,我當時也有這種心情,對電影既充滿嚮往又不明所以。
為了拍攝該片,我和朋友趕工了幾天,用竹枝和宣紙完成了戲中所需的鶴形風箏,沒想到試飛時,不小心摔斷了鶴脖子;隔年四月,我又重做道具,才完成片子的。後來這部短片還幫我申請進入了紐約大學(NYU)電影系。
拍片時我從攝影機的觀景窗望出去,我就知道我應該有天分,因為那個世界跟我平常經驗到的世界是不一樣的,我可以只「選擇」有意思的東西,在那個世界裡,我可以盡情揮灑,並讓夢想顯影、留下。不過那時候舞台做的多,我對兩個都有興趣。
在藝專,影響我最大的就是教授「電影導演」的王大川老師,我三年級時他去世了,我追隨他,因為他學問好、閱歷豐富,我很崇拜他。
王老師是位蒙古王子,以前在東北很有錢有勢,據他說:「光是統轄的國土,就比台灣大二十倍。」二十八歲當上將軍,至俄國、美國求學,都有秘書、隨從隨行,又唸軍校、理工大學,經歷過輝煌的歲月。他喜歡票戲,在國內,捧戲子、跟名角一起票戲;在國外,捧電影明星、送林肯轎車。
初到台灣時,還送了三百輛吉普車及軍備給政府。不過他在教我的時候,可能受過很多委屈,十分抑鬱。我追隨王老師時,他身體已大不如前,住的很破舊潦倒。我有時陪他去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看京戲,有時去給他買麵包,他喜歡明星麵包店的麵包,質感像美國的口味。向他請教任何問題,不論東方、西方,一定有答案。
多方嘗試
在藝專的藝術氛圍下,除了戲劇、電影外,只要是好玩的,我都碰一下。我學過芭蕾,不過時間很短。因為那時編了齣獨幕芭蕾舞劇《阿奇》,換了五個男主角都不成,後來我就自己上場,先去學了一個多月,又演又跳。
當時還寫過一篇一萬多字的短篇小說〈走了樣的焚鶴人〉,述說我拍攝《星期六下午的懶散》的經驗,發表在《藝專青年》上,那是我第一次的寫作經驗。
同時,我還跟申學庸老師學聲樂。記得高中時參加合唱團,每天下午人家掃地我們練唱的一個小時,是我的快樂時光。到了藝專,繼續練聲樂,先跟音樂系學生陳建華練發聲,申老師聽了我的聲音,說我可以練得很好,就破格收我為徒。有時我也和好友余季畫畫素描。
我好像做藝術類都有點天分,不過除了拍電影外,沒有一樣持續下來。電影很適合我,因為它涉及了音樂、舞蹈、寫作、戲劇、視效等因素,我可以在電影裡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變為另一種獨立的表達方式。
近鄉情怯的矛盾心理
我學戲劇、美術,爸爸雖然答應支持,但內心一直很矛盾。
記得二年級升三年級暑假時環島巡迴公演,我們至工廠、軍中演出舞台劇,音樂、舞蹈科也隨行表演歌舞、國樂等,我們演員也會支援歌舞表演充個場面,大夥又歌又舞又搬道具,像跑江湖似的很好玩。一到嘉義,我就開始緊張,因為快回台南了,我也心裡老犯嘀咕的氣自己,在外面本來高高興興的,為什麼一接近家就備感壓力。
踏進家門,老爸一看我因公演累成的黑瘦模樣,就在飯桌上開訓﹕「什麼鬼樣子!」我當時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走回房裡,把自己鎖在門內,這是我第一次膽敢有此犯上舉動,已經是很革命了。
當時父子倆都很不開心。因為在父親的印象裡,我的公演和小時候我們看的軍中康樂隊沒兩樣,他很傷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沒考上大學,居然淪落為給人逗樂子的康樂隊隊員,所以他一直催促我出國,希望能拿到學位,成為戲劇系教授。
直到現在,我格局比較大了,這層心理障礙依舊存在。我回台灣就緊張,搞戲劇,我是跑的越遠,能力越強,人也越開心。一臨家門,緊張壓力就迎面而來。對我來說,越接近生活,我的壓力越大,越難以從事藝術處理,能力越低。
如小時候離開媽媽到花師附小,我就不哭了。離家到藝專,我的能力就有所發揮。在英國美國拍西片較易發揮,一拍國片就心情沉重。在我電影裡,這種心情表達得最明顯的大概就是《喜宴》,以為在海外很自由,但親情又把你抓回來。
想來有趣,返家、離家、壓抑、發展之間的拉扯,都和父親有關。出國是他和我之間的「約定」,離家千萬里即是他的促成。
因為要出國深造,我就做了些準備。本來想去法國,因為那時法國電影新浪潮很吸引人。剛開始我去學了兩個月的法文,但法文裡的陰性陽性、時態,搞得人頭昏腦脹,加上也要通過語文考試,於是改變初衷,有一搭沒一搭的繼續補英文,總算托福勉強過關,我開始申請學校。
由於鄰居小孩在伊利諾大學唸書,回來時說起該校戲劇系有棟很大的劇場,裡面在幹什麼倒是不知道,我就申請伊大。
Upside-Down——文化衝擊
因為當時藝專不是大學,學位只是學分證明(credit diploma),所以我到伊利諾大學戲劇系導演組就讀時,還是轉學生,得從大學部一年級讀起,不但有些共同科目要唸,所有專業科目也都要學。一九八○年順利拿到藝術學士學位。
在伊大第一年,我經歷了兩個天地翻轉的文化衝擊,一是來自戲劇,一是我開始看左派書籍。
第一個「文化衝擊」跟「性」有關。因為當時伊大戲劇系老師所選讀的近代經典劇本,包括從易卜生、荀伯格等人的作品以降,正巧都跟性有所關聯,而且都很強烈。年輕的我便有個印象,「性」是西方戲劇的一個重要根源,精神淵源於「失樂園」。
以前在台灣老師都不明講,到了美國第一年,全反過來,老師談的很多都是性和戲劇的關係。我因而對戲劇原理、東西方的文化差異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在伊大,我感覺才接觸到真正的西方戲劇,整個扭轉了我對戲劇的觀點。
在我的認知裡,以基督教為主的西方傳統中,「失樂園」跟「性」有很大的關係。人類受到撒旦(蛇)的引誘,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園,開始意識到羞恥,有了性交、懷孕,所有的痛苦與生命的延續由此開始。人類對性慾望的覺醒是受到魔鬼的引誘,致使人類犯下原罪而受到上帝的處罰。
西方的掙扎即是人類擺盪於上帝與撒旦之間的拉鋸,西方戲劇精神也以此為出發點。走出伊甸園後,人類開始認識自己,因而求知與創作,知識與創作即是人類對上帝的一種挑戰,也是人性的一種驕傲。在人性與神性的對立中,人要活得有尊嚴,就會有所懷疑,我思故我在。因此,一切知識的衍生也跟痛苦有關,尤其是宗教、哲學的產生,都跟人的磨難密不可分。因為人在快樂順利時多半不去思考,痛苦時,才比較會反思問題出在哪裡。
在西方,蛇在夢中引誘女人(夏娃)而使人類犯下「原罪」,受到性的處罰,在東方就好比七情六慾。西方戲劇喜用「衝突」來做手段,求取淨化與昇華,這似乎跟我們的教養很不同。
記得在藝專時,中西通達、學問最好的鄧綏寧老師教授中國戲劇史時,曾講過一段話,我當時以為是個笑話,在伊大接觸西方戲劇後,才領略箇中道理。鄧老師說:「和尚和尼姑的戲沒什麼好看,但花和尚碰到浪尼姑,就有戲看。」
我們的話劇(舞台劇)、電視、電影皆學自西方,但一般不去摸他的骨。以前王生善老師教我們戲劇概論時,也曾提及電視劇裡演「爸爸打兒子」的情節,一個耳光下去,兒子馬上說:「爸,我錯了!」王老師說 ﹕「戲,就不能認錯,就是要跟爸爸吵,再衝出去,這才叫戲,一認錯就沒戲了。」
雖沒有明講,其實就是「衝突」,就是講個人意圖的最大伸張。「不順」才造成「戲劇性」,戲劇的產生不是靠「平衡、和諧」,是相反的。我覺得很有意思,就在那默默的吸收。
另一個「文化衝擊」就是我離開那時的台灣,才有機會開始看禁書——共產黨的文藝及宣傳作品,尤其是老舍的著作及斯諾(Edgar R. 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
從台灣到伊大,我第一次經歷下雪,也第一次從圖書館借了這些書回來,真是「雪夜閉門讀禁書」,我這才知道﹕「搞了半天,原來我們是壞人。」頭一回,我對自我的身份認同產生了不一樣的觀察角度。這個衝擊對我來說,有如天地倒置。
這兩件事持續影響我很長一段時間。
唸電影選對了路
在伊大,學科、術科並重。學科方面有戲劇史及劇本研讀,術科方面除了學習表演、導演、劇場運作外,每學期還要打卡做滿一二○至三六○小時的劇場工作。除了做劇場工外,我還參加過三次正式舞台演出及導過一次小劇場。伊大兩年、藝專三年,五年的戲劇養成教育,成為我日後電影創作的底子。
當時一眼看過去,我以為最優秀的人才都在表演組,我就有個概念,如果把戲劇剝到最後,用削減法衡量每個元素,哪些可以不要,那麼最後最必要的一個元素就是,一個演員站在舞台上面對觀眾。
過去在藝專,從一年級開始我就演男主角,自小練習的演講經驗,讓我可以口齒清楚,在台上我是有兩把刷子的。然而到了伊大,語言不行就不能演,只能演默劇、小配角,埋頭在一邊學習導演功課,比較沒意思。
那時我開始興起念頭,當導演就要當電影導演。一九八○年拿到戲劇學士後,我同時申請了伊大的戲劇研究所和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
我將轉唸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的想法,徵詢父親的意見,父親本來希望我繼續唸戲劇,拿博士,將來好教書。最後還是同意我唸電影,學費及拍片花銷家裡會幫我。
我一讀電影就知道走對了路。因為我當演員是一種表演,當導演也是表演,藉電影來表演。電影主要靠聲光效果,沒什麼語言障礙,這是我最適合的表現方式。
拍電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時我英文都講不太通,句子也說不全,但拍片時同學都會聽我的,做舞台也如此,在台灣、美國都一樣,不曉得為什麼。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導戲,大家就會聽我的。導戲時,我會去想些很瘋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給做出來了。我想,那麼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麼東西在裡面,也許這就是天分。
真搞創作的,其實沒什麼高深學問。拍片實務是街頭智慧,靠的是臨場的機變反應。可是想法的成形,卻是個複雜的有機過程。
我在NYU拍片後才發現,平常在班上滔滔不絕、分析電影頭頭是道的人,一拍片,你不敢相信那是同一個人,那麼簡單的事情,他都反應不過來。我這才知道,讀理論和拍片根本是兩碼事,是兩種不同的才份。當然,有些人像高達(Jean-Luc Godard)、楚浮(Francois Truffaut)兩樣都具備,但這種人真的不多。
身段高的人常常拉不下臉來放膽一試,較難突破現狀。我覺得人的自尊和他的知識背景有關,而創作多是本能,是打破現成觀念的。
觀念能分析很多東西,可是創作不是觀念分析,創作是運用想像力直觀的去表達一種經驗,創作者本身只是作品誕生的一個工具。
從小學起一路到拍《推手》之前,在台灣升學體制下形成的士大夫觀念,以考試成績為唯一標準來評判一個人的高下,在這種科層裡,我所處的地位始終徘徊在吊車尾階段,反而是一種解放。到了藝專,我第一次可以拋開以往的價值觀,像個新生兒般的重新開始。走上這條路,是一種原始的衝動,非做不可。
在我生活的環境裡,我的自尊一直很低,從台南一中起我就覺得不如人,到了藝專,社會上又覺得不是間好大學。畢了業,服兵役剃光頭,又被女朋友甩掉,女友進入社會往前走了,我還是阿兵哥。
到了伊大,都是美國人,話也聽不太懂,朋友也沒法交,個子比老外瘦小,中國留學生又多是理工醫農的高材研究生,我是唯一唸戲劇的大學生,雖然努力的吸收,但仍自覺處於很低的位置,要進入世界闖出什麼,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電影系,就不一樣了。
我最愉快、最充實的日子,就是一九八○年到八三年在NYU的求學時光。一拍片就很快樂,會想很多點子實驗。有時學校經常放猶太假,我搞不清楚,到了教室一個人都沒有,我第一次覺得放假心裡不高興就是在NYU。以前上學放假是最高興的,現在不想放假是因為心裡想學,想多知道些。放假不上課,我覺得損失了一天,心裡頭真的很在意。
NYU電影製作系研究所的訓練算是很紮實,三年裡把電影的前置、後製都摸過了,通常畢業作得花上額外的一年時間完成。每個學生要編導五部作品,包括默片、音樂片、配聲片、同步錄音片及畢業作。這裡以栽培導演為主,上課時,有時老師在課堂上講解名片的結構與拍法,但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拍片及討論彼此的作品。
拍自己片子時可練習創作過程、領導統御及被批評時要何以自處。幫別人拍片時,則有機會觸及各部門的基本技術。雖然都是入門,但我學到了初步的整體製片及導演的概念。
紐約大學期間,我拍了五部電影,二年級拍的《蔭涼湖畔》曾獲金穗獎最佳劇情短片及NYU 的獎學金。我受到肯定,再接再勵,用盡手邊一切資源,籌拍了《分界線》(Fine Line)。
敘述紐約運河街南北分別住了不同種族的人,一邊是華人、一邊是義大利人,因某事引起兩種人在紐約四處流竄,以故事搭配我在紐約各處拍攝的街景。為了這部畢業作,我自己打工、父母資助、女友惠嘉贊助,共花了一百多萬台幣。
記得拍攝《分界線》的頭四天,我興奮得睡不著覺。到了最後階段,還差八千多美金,我就從惠嘉的帳戶裡直接提了來用。那時她在伊利諾大學當助教,因為要交稅,所以存摺放在我這裡。奇怪的是,我一點都沒有愧疚感,事後我跟她說起這件事,她也僅只「喔」的應了一聲,表示知道了。
從「缺席」到「榮譽博士」
一九八四年的畢業典禮,我沒出席,和 NYU 的同學羅曼菲、劉靜敏、平珩一起到劉靜敏所住的大樓屋頂水塔旁,照了些碩士照,碩士袍還是平珩租來的,大家輪流穿、照大頭照,寄回家交差。
十七年後,二○○一年五月十日,母校NYU在第一六九屆畢業典禮上,頒給我榮譽博士學位,彌補了當年缺席的滋味。我想父親心裡也會很高興,因為他向來希望我多唸書。
典禮是在紐約華盛頓廣場舉行,在場觀禮的有穿著紫色長袍的五千名應屆畢業生及一萬多位家長,NYU董事葛利撤(Mr. Gleacher)引導我們五位榮譽博士上台,藝術學院電影、電視系主任柯曼(Julie Corman)在致詞介紹前,也用中文向我道了「恭喜」,隨後由校長奧立佛(L. Jay Oliver)頒發證書,葛利撤為我佩戴象徵榮譽學位的披帶,教務長史戴曼(Harvey Stedman)為我戴帽子。我揮手致意,謝謝大家的抬愛。
返回母校,看到學弟妹,心裡很高興。代表致辭時,我開玩笑地說,在學校學了很多,但我大部分都忘了,只有一樣難忘,就是不斷學習、勇於嘗試及面對失敗。
NYU的環境是孕育我成為電影人的開始,在這之前,我沒有碰過電影,都是弄戲劇,拍片也只是玩票。沒想到碰對了路,就一直走下來,也沒想過要轉行。
對我來說,學校畢業後才碰到真槍實彈,還沒有被打死的話就學些經驗,繼續往前走。
NYU的教育方式很務實,我學了不少實務,都是吃飯的傢伙。我覺得新的國片常常瞧不起技術,但在 NYU 時沒有這種心態,就是一種求生訓練,大家機會均等,一起出去拍片,各部門的技術都摸得到,但不專精。同時還要學著當領袖,讓人聽令辦事,那時是領導三、五個人,現在領導三、五百人,但原則類似。
我一拍片就會忘我,像變了個人似的。其實「導演」(Director),就是給方向(Direction)的人。從學生時代起,我拍片就有個目的,想練習一樣新技巧。學生階段,我沒有特別的想法想表達,職業拍片後就有話要說,而不再只是練習新招了。直到現在,我還保持這個習慣,每拍新片總希望能觸摸一些新技術。
基本上我拍片的胃口很大,有很多好奇心,學到某個技術,就會有快感,而且我希望做出不同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我就有很大的滿足感。(資料提供:李安)
文/張靚蓓 2002/11/20 15:31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lovechang 的 bbs 電影板精華區
Copyright © 昔影.惜文. Template created by Volverene from Templates Block | Blogger Templates | Best Credit Card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