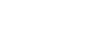發信人: RAYBO@kkcity.com.tw (丰狂無几), 看板: movie
標 題: 幽靈人間--談社會變遷中的邊緣人
發信站: KKCITY (Thu Nov 22 14:15:02 2001)
今年的港片在《少林足球》與《幽靈人間》分別奪得票房冠軍後,港片復甦的氣氛顯然可見,在經濟景氣低迷的香港社會,這兩部片子分別從不同的態度用透視鏡來為社會注入一劑強心針!《少林足球》的成功固然與周星馳的魅力與絕佳的劇本有關,但其務實的角色與勵志的題材更是鼓勵社會用熱情與理想去「踢出個未來」。
不同於《少林足球》把鏡頭對準繁華熱絡大樓林立的銅鑼灣,《幽靈人間》把故事拉到西環市井的角落;《少林足球》中的市井小民奮力從社會底層打入資本階級的球場,《幽靈人間》則赤裸的描述社會的邊緣族群茫然與無奈的困境。
沒有了雄偉的時代廣場,幽靈穿梭在傳統市集,讓我們不禁懷疑貧富差距在面積僅有千餘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七百萬人的彈丸之地竟也是無可避免的結果,同樣一個社會有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尤其在比較《少》片與《幽》片後,果真是人間(社會上游階層/都市化/政經重地)與靈界(社會底層/老舊建築/傳統市集)同處一地。
而代表著中產階級與都市進步象徵的大眾交通系統「電車」,則是穿梭「陰陽」兩界的往來樞紐,許鞍華很巧妙的暗示了兩種代表不同階層的交通工具所造成的結果---
Peter一群人到東堤與護士們聯誼,在晚上一個人閒晃時差點被飛奔而過的腳踏車撞到,相對於只需對著呼嘯而過的腳踏車破口大罵,在汲汲營營追求金錢的社會,穿梭的路人只要稍不注意就會被資產電車碾掉了頭,而故事就在象徵都市化的電車碾斷了黃秋生扮演討債人的頭之後開始了。
從角色來看香港的社會變遷:
片中不僅反映著香港的階級差異,也從舒淇所飾演的一角帶出了香港與大陸的情感糾葛。
一位被人蛇偷渡到香港的小女孩,因目睹了一件意外而擁有了陰陽眼的能力,在此片中的「陰陽」象徵社會的上下層階級,「陽」代表著社會的繁榮,「陰」代表著社會的邊緣。
而這位從大陸來的女孩則是一上岸不久就失去了在大陸的記憶,這位落處於香港的大陸女孩看穿了這社會所存在的陰陽兩界,結果為了躲避與面對社會下層/邊緣/落魄(鬼魂)的恐懼,只好戴上眼罩假裝有鬼魂(下游階級)的事實不存在,於是在社會中驚慌茫然的流竄著,眾人卻不知她究竟害怕著什麼。
雖然看不到可以減少她心頭的恐懼,但她也不得不向Peter---這位從小出生於繁榮社會的市井小民---點明這個事實「鬼在那裡?」「每個人的附近都有一隻」。
面對著資本社會的壓力,深怕自己成為社會邊緣人的恐懼,是每個人心中的陰影,都市化的電車不停的向前急駛,每個人爭先恐後的想搭上車,唯恐成為落後與窮苦的象徵,從大陸落地到香港的June戳破了香港人的深層恐懼。
《幽》也傳達了身處其中的年輕人他的不安與矛盾。Peter代表著戰後嬰兒潮的Y世代族群,他揚棄傳統的名字「旺財」,他認為這是上一代對他開的一個玩笑,他更嘲笑著他哥的名字「盧安達」---一個代表貧窮與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
他唾棄傳統價值,卻找不到如何跟上社會進步的軌道,只好在西化的社會中,次文化族群聚集的場所「搖頭店」裡閒逛打混,而X世代族群所代表著積極與理想的特質已成了落後的上一代價值觀,但X世代與上個世代所積累下來的財富卻養成Y世代與下個世代安逸與享樂的人生觀。
許鞍華更將視角延伸到下一代---一位看著色情漫畫在理頭髮的小孩子,在Peter不小心剪到他的耳朵後,竟因看到血而高呼「正點!」,導演很不保留的將從小生長在嗜血暴力與色情環境中的小孩子所面臨的問題點了出來,但兒童真正被犧牲的一場戲卻是因為小松的父親去大陸經商、包二奶下,在家庭的衝突中墜樓而死。
大陸市場不斷的衝擊兩岸三地的社會,中產家庭在這一波衝擊中更是不知如何自處,面對資本社會造成兩代疏離的病症終於在小松一家爆發,而小松滿臉的血正是許鞍華對於忙於賺錢忽視家庭倫理的現代社會最強烈的控訴!
相對於小松小琴一家,Peter的處境算是較好的,他的家庭背景是在傳統市集裡擁有一家蛇店,但在市場變遷下也不得不結束營業,改販賣符合消費者口味的小吃店維生,而出身於蛇店的Peter卻是非常怕蛇,在June(小琴)面前更是第一次抓蛇,可說是完全的跟傳統技藝隔離的人。
他是社會轉型中的新新人類,若小松一家反映著新市場的開放,Peter一家則反映著舊時代的結束,市井小民在面對著這幾年社會急遽轉型的當口,不得不調整腳步以應對整個變遷的局面與困窘的處境,而Peter從事髮型設計師的技藝,正是社會轉入以消費與流行等服務業為主的後現代社會最佳的代表,因為理髮業正是為了保持一個人的鮮度,並隨時汰舊換新的一個行業,伴隨著流行文化的到來,髮型設計正是青少年追求流行跟上社會腳步最有力的象徵。
黃秋生所扮演慘遭被斷頭的無頭鬼,則是資本制度下變形扭曲的地下社會代表,同樣是社會的邊緣人,他卻代表著另一股壓迫勢力,他的身份是一位放高利貸的討債人,他的命運正訴說著在社會變遷轉型下,慘遭斷頭的邊緣人,他們不被社會所接受,雖然被社會排斥,但他們仍以另一個與法治相抗衡的方式生存在社會底層,並以壓迫同在社會核心外緣的階級為生。
他所附身的Peter,不正是暗示著變遷中的社會,時下青年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無可避免的被打入這群冤鬼中,成為地下勢力的一份子嗎?這代表著地下勢力的無頭鬼殺掉代表傳統價值的Peter 之父,也附身到Peter之上想毀掉Peter,他跟二奶的亡魂搶奪象徵傳統家庭倫理的小松母親的身軀,也附身到神棍的身上想來殺掉Peter。
這位神棍的身份也很特殊,他原本是位皮條客,出獄後改從事神棍一職,而他做神棍「純是市場需求」,自己卻不信鬼,但一遇到鬼時卻又是穿起道袍口念符咒,實是一點能耐也沒有,神棍代表著在社會底層因時變化的邊緣人,藉由投機取巧以在這夾縫中尋點生存的空間,但也是隨時會淪落為被地下勢力附身的邊緣人。
無頭鬼也附身到June身上,但從Peter喊出「她是無辜的」一語中,似乎是許鞍華對於落居(偷渡或透過關係)到香港社會的大陸子女淪為地下勢力的侵襲感到同情吧。
我們知道在九七前大陸就不斷有「內地人」偷渡來港,九七後更有透過婚親關係到港定居,不僅為香港帶來新的社會問題,暴增出來的人口也未必真的享受到香港的進步與繁榮,更可能成為社會的邊緣與法治外的地下族群的一員,這個問題一直是香港的隱憂之一。
角色的職業也反映著這社會階層所代表的符碼,如Peter的髮型設計師代表著流行的消費文化,是個揚棄傳統家庭出身,期望能跟上時代腳步的新新人類;June的護士一職則是在生死(陰陽)間居中斡旋的角色,她在階級中的曖昧關係,又正如她是個從小就遺落大陸的過去,既非道地的香港人,也不再是原本的大陸人,而是在社會中漂流的異鄉人一般的曖昧。
其他的社會下游階層的職業又有守著傳統市集店面的老闆、高利貸的討債人、神棍等等,井然有序的變成一條地下社會的食物鍊,有掠食者/肉食動物(討債人)、供應者/草食動物(傳統店舖
)、雜食與腐食動物(神棍)、維持生態循環與救助的角色/植物/陽光/空氣/水(護士)。
而Peter所代表的髮型設計師顯然的與這個環境格格不入,但他卻落入了這個環境中,所以他在戲中幾乎完全在狀況外,渾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既脫離了傳統,卻又跟不上資本社會,最後仍是靠著擔任救助者的June幫他脫離了險境。
從情節安排來看時代變遷下的社會:
無法抗拒與不知緣由的宿命論充斥著整片,可惜這場債來自一個撿零錢的舉動,卻糾纏了十五年,這段無緣早日解釋的誤會由戲中的一場輕鬆的橋段引出---
=================================================
Peter上車後見司機不開車,怒氣沖沖問司機:
「那你幹麻停在這裡!」
司機:「車子不能動,當然只好停在路邊,
『剛好』你們兩個站在這裡...」
Peter:「那你可以叫我們兩個不要上車啊!」
司機:「你們兩個『動作那麼快,我那阻止的了』!我可以阻止你
們一下就講個不停嗎? 我還沒機會告訴你們』車子已經壞掉了!」
================================================
無頭鬼最後得知自己的死因竟只是因為剛好站在那裡,被後面的Peter父親推到,而Peter父親卻是被一個彎腰撿零錢的不知名的人推到,一切都來不及解釋,也無法阻止,卻害了Peter一家那麼久,事情的答案竟如此可笑與無奈,只能倉然失笑。
我們的社會不就是如此嗎?在金融經濟所控制的遊戲規則下,牽一髮動全身,尤其是在20/80法則中--百分之二十的人決定百分之八十人的事--誰知道是那個階級的人為了幾塊蠅頭小利結果害不相干的旁人橫死街頭呢?
大環境的蝴蝶效應使得每個人都身不由已的在社會各階層中穿梭、甚至改變身份(人/鬼),誰又知道真實的背後答案與事件的起因竟是與我們毫無關係的人,人力之微在社會底層顯得渺小而無奈,於是有人渾渾噩噩、有人強取豪奪、有人投機取巧、亦有如Peter之父者,堅守自己的本份來接受他的命運。
但許鞍華則透過無頭鬼附身到每個底層角色的身上大聲的吶喊「還我頭來!」,這顆頭代表著生命與尊嚴,卻被象徵經濟與繁榮的電車一碾而過,這種被錢壓得喘不過去的無力感迫得無頭鬼非討回他失去的「頭」不可。
許鞍華在處理這場戲時,用掉落在地上滾動到電車底下的紅蘋果,巧妙的象徵了斷掉的頭顱滾落的情形,「蘋果」這個符號意涵一向有生命力的象徵,代表了創造、健康與希望。
在片頭一開始便是小女孩手拿著蘋果從大陸來到了香港,而掉落的蘋果正是象徵著被斷頭的下層階級的頭顱,而Peter之父在住院期間嚷著要吃蘋果正是為了還想保有生命與健康,但最後仍不幸的在下層社會中的衝突被討債鬼討掉了生命,死前手裡還拿著蘋果,卻無法再吃上一口。
「我今天就是為了等這頓飯!」傳統價值的殞落除了Peter父親之死外,亦在頭七時飯局上,由另一位社會的新生代--Peter的姪女翠兒--破口而出,這種不識大體的態度與傳統喪禮的頭七逐漸在新新人類中喪失意義,許鞍華亦用鏡頭冷冷的斥責了一頓,在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與傳統價值的凋零,中生代感到無力新生代卻顯得無知與迷茫。
導演所想要表現的價值觀:
從劇中角色的死亡,突顯出社會中的人被何者所壓迫--Peter之父被地下勢力所壓迫、無頭鬼被急駛的資本社會所壓迫、小松與二奶被變遷中的家庭結構所壓迫,這些角色都是因社會的結構變遷而遭逢不測,只有小琴是為情而死。
小琴這個角色原本純粹是帶出小松一家的變卦,並為戲裡注入愛情的活力,戲中的每個角色都是受社會壓迫的邊緣人,整日茫然若失,不知為何而活,只有鬼魂反倒是目標堅定,一個為索命而來,一個為愛情而來,這兩隻鬼魂因為有了目標而堅定自己的信念,表現出旺盛的活力。
反倒是在影片開始的搖頭Pub裡,許鞍華意有所指的用「群魔亂舞」畫面帶出這群「搖頭族」在那裡呼口號搖頭熱舞,暗示著時下青年在這個社會的迷茫。而小琴在死後透過附身來傳達她對親人的感情與對愛人的思念,比起Peter在面對感情與親情時顯然是主動多了。
許鞍華在諷刺了這個社會之後,也用鏡頭描寫她對親情的強烈關懷,她以Peter面對父親表達感情時的兩場戲中硬生生的以恐怖畫面來截斷剛積蓄好溫情流露的戲份,一場是父親突然出現在房間拿巧克力給他,鼓勵他,卻突然接到父親吊死的畫面;另場戲則是Peter終於打破與父親間的心結,卻突然驚見無頭的父親,原來已是夢一場。
父親與Peter在現實中與父親的對手戲可說是沒有真正真情流露的時候,到頭來只有夢中對親情的幻想,許鞍華用這兩場戲來交待親情可說是警世之深,似乎在告誡觀眾晚了就來不及了。
而在Peter與June的露水姻緣還是Peter與小琴的交往,我們很難了解Peter在對方的同一具軀體中愛的到底是誰的靈魂,而相對於這段感情的曖昧性,我們更可鮮明的了解許鞍華導演在傳統價值與社會變遷還有什麼是不變與可控制的命題中,也只有親情與家庭倫理是可貴與不變。
結論:
這雖然是許鞍華導演對香港社會的觀察,但對於在資本巨輪中轉動的社會來說,更可驗證在舉世每個資本國家的角落,社會階級與貧富差距的對抗,人口遷移與社會邊緣的雜處。
在地鐵與大眾捷運系統發達的都市叢林中,家庭網絡比電車上的人們更加的疏離,而社會急遽的變遷時至今日已轉為一種動態中的平衡,階級不再是恆久不變的僵化模式,誰難保不會被踢出社會的核心淪為社會中的邊緣人,如何因應這個變動的社會來自處是新一代社會人的重要課題。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lovechang 的 bbs 電影板精華區
Copyright © 昔影.惜文. Template created by Volverene from Templates Block | Blogger Templates | Best Credit Card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