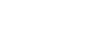發信人: shaman.bbs@ptt.csie.ntu.edu.tw (女子有行), 看板: movies
標 題: 傾城之怒-關於《惡女列傳》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 (Sun Aug 15 23:15:50 1999)
惡女不是天生的,而是一個生成的過程。《惡女列傳》說的就是這個過程,第一段「板凳天后」,愛表演的范瑞君很努力的為自己找觀眾;第二段「猜手槍」,落翅仔蔡燦得捉弄警察、擁槍自樂;第三段「阿狗阿貓」,賈靜雯操弄著一個陌生人與陌生狗的命運。
惡女們年輕氣盛,她們的成長故事不是純情青春夢,而是一段尋找自我、建立主體性的旅程。她們惡形惡狀發洩著對世界之怒,往往下手過重,用力過猛,但即使一座城市為之傾覆,她們恐怕也不會罷手。
蔡燦得演的阿彩是片中最有力道的角色,她的演出令人肅然起敬,簡直是小甜甜演陳文茜。
在標榜清新、寫實的台灣新電影裡多的是苦悶少男,以暴力(熟悉的打群架的場景)與性(例如成功的偷窺或不成功的嫖妓)為青春的出路,卻少有主體性強烈的反叛少女,我只依稀記得李明依在《童黨萬歲》裡演過這樣的角色。那時,進行多樣情慾試驗的李明依秀出了豪放女滿不在乎的架式,現在,蔡燦得則以更為挑釁的姿態,表現出她對整個世界全面性的不耐煩。
男女、師生、警民、老少,這幾組關係裡,阿彩每一樣都居於劣勢,但她反正無可損失,索性睥睨一切,宛如烈士。她豐富的表情讓我們具體看見一個深邃的青少女世界,憤怒、頹廢、孤獨、迷惘、致命的聰慧,為了內心風暴,可以亡命天涯。所以她需要嗑藥,因為只有她睡著,天下才會太平。
舉槍的最後片刻,她不發一語,但哭出一種難以排遣的悲哀,渲染得讓我們也難以釋懷。因為她的深刻演出,這一場哭戲成為片中美好的空缺,適當的留白。一個剪裁得宜的故事,餘味無窮的結束在一個灰敗的頂樓上,一把破藤椅裡。
然而阿彩的角色是幽默的。你看她多麼會用衛生棉。嗑藥時戴著滴了紅藥水的衛生棉,以免發生不想發生的性行為;整警察的時候把衛生棉當便條紙用,還有背膠呢,剛好可以貼在頸後。房裡掛人盪呀盪,門鈴是警鈴。
她什麼不好偷,就偷警察的槍,然後寄張香豔照片給警察,警槍黏在裸體模特兒的私處:「有槍很屌嗎?」在衛生棉與槍的對峙裡,阿彩把性別隱喻翻新好幾回,衛生棉從不吉祥變成很幽默,槍從很神氣變成也很幽默。
在一個逸出常軌的惡女身後,是一個很少入鏡的破落台北。昂貴的電影工業很少有平民視野。我們曾經看見過華麗詭異廣告一般的台北,在《只要為你活一天》;現在跟著阿彩的身影,我們看見了環河南路怪天橋,令我想起已經拆除的中華商場;鏡頭裡坑坑洞洞的西門町已經被翻修過,鋪上體面的行道磚了。
而「板凳天后」莉莉雖然出入名店穿著時髦,但最後一幕從對面頂樓回看她的家,那彷彿才是下了戲之後的真實─一樣是外牆滲水鐵窗鏽蝕的、典型台北公寓。
「板凳天后」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竟然是同性戀。驚訝嗎?回想一下,莉莉的演技從頭到尾沒有被珍惜過,她那熱過了頭的表演慾,從來都帶給她挫折與難堪。經紀人懶得理她,大導演被她嚇壞了,演員前輩開導她,連對面的偷窺狂都沒在看她。從頭到尾只有一個人讚賞她的演技、被她的表演取悅,就是片子裡的大明星林心如。
莉莉當臨時演員的時候穿男裝演男人,中午休息吃便當,她坐在大明星林心如前面,故意往地上啐一口,一副粗魯樣大搖大擺。林心如嬌滴滴的掩口笑了,穿襯衫西褲的莉莉走過林心如身邊突然一記回馬槍轉身:「很像吧!」她們重逢的時候,這段粗魯的表演就成為她們之間的暗語。
一想起初遇的情景,林心如的回應是熱切的、嬌俏的,立刻以手中的試鏡劇本向莉莉示弱兼撒嬌:「我怕我放不開。妳好像很放得開耶!」
這是唯一的一次,莉莉選對了觀眾。她為她表演,而她報以讚賞與信任,甚至帶著一點崇拜,一點依賴。莉莉以那場性別越界的表演,為自己贏得了一個知音。也許莉莉成為「最佳女主角」的機會不在演藝界,而在另一個女孩的生命中。如果我們的板凳天后能夠理解到這一點的話,她就不必在末尾空虛困乏的大哭,而應該約林心如出來喝咖啡,耍寶逗她開心囉。
相較之下「阿狗阿貓」裡的小綠與小平似乎幸運許多,她們的人生有彼此作為知音。她們的兩人關係沒有分化出明確的T婆角色,或者根本應該說,這兩個角色的塑造刻意泯滅了任何可能被詮釋為T婆的女同志符號。
兩人留著類似的髮式,穿類似款式的衣服,一起打籃球;這個騎機車,被載的那個就以跳馬
背的姿勢上車,兩人之間仍然維持適度的陽剛,等量的瀟灑。她們的感情關係處理得十分低調,雖然同居、形影不離、在沙發上玩得倒在一起,可是情感的互動卻著墨不多。
「板凳天后」裡無心插柳的一段互動滿溢著同性戀情愫,有實無名;到「阿狗阿貓」被反而抽空了內容,同性戀身分也只能迂迴交代。是碰巧沒有明說、不想明說、不需要明說,還是不能明說呢?在《喜宴》的時代,男同志至少還可以向媽媽和觀眾現身,然後和爸爸虛與委蛇即可;如今《惡女列傳》可惡不可言,豈不可惜?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88.08.15 ⊙張娟芬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lovechang 的 bbs 電影板精華區
Copyright © 昔影.惜文. Template created by Volverene from Templates Block | Blogger Templates | Best Credit Card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