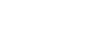發信人: wheel.bbs@bbs.cs.nccu.edu.tw (地球之夜), 看板: movies
標 題: 【人物專訪】魔法阿媽
發信站: 政大貓空行館 (Sun Mar 21 02:10:14 1999)
時間:三月十七日,下午一點半
地點:台北,cafe odeon
出席訪談:王小棣(以下簡稱王)、
麥仁傑(以下簡稱麥)、盧非易(以下簡稱盧)
編撰整理:郭政倫(s8406@cherry.cs.nccu.edu.tw)
盧:為什麼要做動畫?
王:為什麼要做動畫?(笑)我覺得遠因近因很多啦,如果說精神感召的話,可能還是宮崎駿。我最喜歡的就是「魔女宅急便」。
開始時,小女孩在河邊,聽著收音機,風吹過來。後來,等不到朋友,小女孩飛起來,就走了,帶著她的貓,去完成她的訓練,整個故事很乾淨這樣。你看著,莫名就會想起你小時候也過過那種日子,也有等在河邊,等不到朋友這一類經驗。
還有,像「螢火蟲之墓」,那男孩靜止在那邊,在人鬼界上,想他的妹妹。我第一次知道動畫不一定要一直動的,被那畫面震懾到了。這樣安靜地講故事,當然是很感動。
這是最主要的鼓勵或說刺激吧,覺得太棒了,其實東方人要能說起自己的故事是很精彩的。所以我就想,台灣的故事也能很精彩啊,尤其是黃黎明(編劇)看到自己的媽媽作阿媽時,那種經驗其實是非常有趣而有感情的。我覺得比起實拍,卡通動畫可能是一個更開闊的世界。
盧:台灣幾十年來幾乎沒什麼動畫片,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麥:台灣的動畫界一直都在作國外的加工,這的確幫助訓練很多一流的專業人才。但一部動畫片需要很高的成本,動畫公司如果想自己拍片,就會變成業務與理想無法兼顧。
如果抽掉最好的人去製作一部片,其它正在趕工的工作可能就會出狀況。台灣一直處於這種情形,同時也一直找不到好的創作方式來製作動畫片,這些可能是原因之一。
盧:妳的上一部片子「飛天」已號稱是九0年代最困苦艱難的製作了,這部呢,相較起來?
王:更有甚之!(大笑)。作卡通的朋友早都警告我們。可是因為我們不懂,所以就不害怕,覺得那就做嘛。可是到了後來,你知道它實在是太多細節了,要那麼長的時間拍一部卡通是一定有它的原因的。大家真的沒看到我們那個時候的慘狀。
人力少,經費少(訪者註:此片經費約為香港同行的四分之一,所耗時間為美國動畫片的三分之一,支援人力則大概是一般的十分之一),除了麥仁傑外,我們都沒有經驗,現在想想也不知道是怎麼熬過來的。
麥:卡通最困難的只在方寸之間的一張桌子上,外人看可能只覺得是在作畫而已。像王導演就很樂觀,我覺得這不可能做出來的,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的,有經驗的人都會說不可能。她說可以。我只好欺騙自己,騙自己試看看,雖然沒有人作過,是不是我們來作看看呢。現在看,很多紀錄是這樣打破的。真的好累喔。
盧:可是法國一位選片人說這部片可以稱是台灣的高甸勳。
王:現在事情過了,再來看會比較清楚。其實,過程中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大家都要咬牙忍住,要說服對方,希望能夠把最好的東西作出來。堅持一下還是對的,這可能是很重要的成長經驗。這種經驗和原創的合作要繼續開擴,正是「魔法阿媽」的意義。
盧:你拒絕了迪士尼的招手,甘願在台灣創作。為什麼?
麥:要賺錢的話,繼續做卡通就好了,因為你只要達到外國雇主的要求就行了,老實講這不難,只要你有一定的能力。可是,有一樣你永遠沒有辦法滿足,你自己的想法沒有被說出來,永遠都是依別人的指示在做事。所以在金錢報酬和創作欲望上,我個人的選擇是畫我自己的東西。我相信從事動畫工作的人都會有這個想法。
我接觸過很多這樣的同行,都很想參與「魔法阿媽」這樣的工作。但國人自製動畫片的機會很少,所以他們練成了一身武功,卻沒有人知道,沒有地方發揮,這是很寂寞的。
王:在動畫加工旺季的時候,他們一個月可以賺十幾萬(麥:大概十年前就可以這樣了)我聽過一個前輩說,以前最高一個月可以賺到一百萬!用百萬算!但我們也有看到像麥仁傑這樣,維持很簡單的生活,堅持畫自己的東西。我真的看到一個人對自己的抉擇。
盧:電影圈也有這樣的,丟下一個月三、四十萬的工作,整年不接廣告,就為了來拍這幾乎沒錢或是賠錢的電影。他們願意犧牲,來完成一個夢想,但是我們的業界、政府、觀眾,我們整個社會,連這樣的一個機會都不給予。回到這部片子吧。
過去你合作的演員都是整個人的合作,但這次合作只是聲音的部份,有什麼差別嗎?
王:我們非常幸運地找到這幾位小朋友,尤其是配豆豆的小朋友,他非常專注,大家聽到影片裏面豆豆哭的時候,他在錄音間是真的哭。我說戲時,他很用心聽,而且真的被觸動了,他不是演戲,因為他聽的時候,眼睛就已經有點紅,很敏感的小孩。
文英阿姨以前常常合作,當我們開始畫人物時,小麥心裏就已經有文英阿姨的影子(掩嘴:不過文英一直拒絕承認影片的阿媽有像她)。
盧:動畫配音是很難的,演員既要對準畫面上的口型,又要表現情感;同時,又是長時間非常辛苦的工作,你如何與這麼多的小孩工作?
王:小朋友一多的時候,那就很頭痛了。當時場面真的很好笑,小朋友是不管你想得到或想不到,他都作,尤其是那麼多小朋友在的時候,真的是很可怕。
麥:錄音室裡,罵人的時間比安靜的時間多。
盧:那導演怎麼折磨你?(轉向麥)
麥:喔…(一愣)。反正真的很慘,做到後來,變成只要讓我睡覺,要我怎樣,我都願意。
盧:這部影片一直在網路上被熱烈討論著,很多年輕朋友質問,為什麼它被提名入圍了金馬獎最佳動畫,最後竟「從缺」。事實上,金馬獎是一旦有影片入圍。該獎項就不從缺。因為,如果評審覺得不好,在入圍階段就不要讓它們入圍。這已經是維持多年的慣例。
今年入圍和決選是同一批評審,為什麼他們不維持這個慣例?請問,從入圍到決選中的那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
王:麥仁傑,你做了什麼虧心事?(眾人笑)
麥:要完成一部作品很不容易,適時的鼓勵是很有意義的。在台灣做動畫片簡直是困難中的困難,有多少動畫片想法是真正堅持下去而拍出來的?幾乎沒有,因為它有種種的不利條件。今年很難得,有兩部,而且類型不同。
我個人的看法是,你不給「魔法阿媽」無所謂,你可以頒給另一部啊。為什麼讓影片入圍,然後從缺,之後又振振有詞再來解釋一大堆,真有問題,之前就沒想到嗎?我覺得這很不專業。
王:(笑,無奈貌)啊,真不好意思,大家真是讓我給拖累了,這可能因為我在電影圈內的一些活動(訪者註:應是指王小棣於此期間成立「電影創作聯盟」為導演爭取創作機會之事),惹怒或得罪了一些人。
大家辛苦工作,如果真的是跟我的這些活動有關的話,第一個就是覺得真不好意思。另外一個,我得說我的臉皮很厚,我只會被我尊敬的人傷害,如果不是我很尊敬的人,講什麼我都不是很在意。
盧:另一點,網路上也紛紛討論評審為何以「迷信」為由而決定從缺。
王:有時候想起來,我也有點生氣。你們不要再說我的阿媽是迷信,我覺得那是有差別的。那樣說,真的是矮化和醜化。我想請問,誰家的阿媽沒有信仰?不管是哪個宗教。尤其阿媽她們走過的那個年代。當你說它是迷信、反智的時候,我覺得你會誤導觀眾對台灣女人和台灣生活的解讀。
我覺得台灣的阿媽的確是敬天畏神,的確是常常在走廟。她們那個時代沒有什麼可以靠,只有天可以靠。我想這個就是最好的形容。
麥:我很欣賞印地安人的一些講法,他們認為什麼東西都有精靈存在,所以他們對大自然有份尊敬。可是現在的人不是,現代這一代幾乎都是受西方教育,當他們看好萊塢電影時(例如「埃及王子」)可以覺得很美,為什麼當有自己台灣人的神話故事時,卻覺得這個迷信。
盧:這裡,我摘錄兩則網路上的討論供參考:一位說:「我們為什麼要灌輸孩子真實的台灣是很俗、很落伍,上不了台的」。另一位回答:「每個民族都有它的神話和傳統習俗,為什麼我們可以把別人的東西看成是文化,自己的就鄙視」。
換個話題:這部影片的行銷,恐怕是我們見過最奇怪,也最辛苦的。好像象徵了台灣電影在滅頂時的掙扎,幾乎所有為求生存的掙扎手勢我們都看到了。為什麼會掙扎到這個地步?
王:國片的宣傳非常少,連登電影版預告片的小欄目都登不起。常常是觀眾都不知道,它已經下片了。同時,好萊塢的勢力越來越大,以前國片還可以勉強排個檔期,近年來國片已經不用講檔期了,好萊塢的空檔就是你的檔期,而且還隨時拉掉你。
但我們這次嘗試拿著片子給戲院老闆看,讓他親眼看到品質,一家一家這樣坐下來談,真的有幾家被說動了。不過,台中還在作最後的掙扎,因為老闆怕被台北的發行商、排片人杯葛,怕以後不給他好萊塢影片,所以還不太敢。
盧:所以這部片子是在片商、戲院種種勢力中努力突圍(王:對),政府在這過程中有沒有什麼幫助?(王:?!)
麥:政府的演技依然沒有突破,他們依然扮演他們的角色。
盧:如果十年以後提到這部片子,你第一想說的是什麼?
王:那天我們在中國時報試演的時候,有一個女孩子是從花蓮來的。我後來知道這個女孩子也會自己上台北來看職棒和職籃。這說明了台灣的消費型態、生活興趣和品質正在改變。任何行業都要面對因為這種改變而來的挑戰。
最近大家在談電影的時候,還是存著很悲憫很可憐的口吻;可是我想說的是,各位,不要總是把國片看成是殘障。每行每業遲早都會面臨挑戰,我們要互相打氣,交換新的行銷經驗。我覺得大家可以用這個角度來看。
盧:幾乎台灣所有劇場、電視、和電影圈的朋友,一聽到王小棣老師,都會先吐個舌頭。你可以想像他們過去的慘痛經驗,但是不知為何,每個人又都熱切希望再和她合作,你呢?
麥:我沒有吐舌頭,我只有咬緊牙關(眾笑)。我想會,第一、她尊重夥伴;第二、她永遠比你更辛苦;第三、不管看來如何不可能,可是,你可以相信,最終,她會帶著所有人完成那個夢想。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lovechang 的 bbs 電影板精華區
Copyright © 昔影.惜文. Template created by Volverene from Templates Block | Blogger Templates | Best Credit Card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