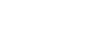發信人: lifefair@kkcity.com.tw (曾經愛你永遠愛你), 看板: movie
標 題: [影評] 《無米樂》台灣的心肝 文/藍祖蔚
發信站: KKCITY (Sun Jun 5 00:45:02 2005)
《無米樂》,2005最好看,最有人味的一部台灣電影。
顏蘭權和莊益增拍攝的《無米樂》是台灣紀錄片,不,更應該放大成為台灣電影的驕傲。因為它的生命力與藝術成就遠比一般的劇情片更強猛。
《無米樂》的生命力來自電影中的每一位農民,《無米樂》的藝術成就來自顏蘭權和莊益增對於拍攝題材的理解、深入,同時找到最適切的表現模式,讓農家歲月的甘苦得能以最達觀、最鮮活的方式展現出台灣人樂天知命的真性情。
紀錄片和劇情片一樣,都是用攝影機來訴說人的故事,都需要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有一定的默契。差別在於:劇情片的幕前幕後工作者共同致力來奔赴或圓滿一個虛擬的共同理念與境界;紀錄片的拍攝者則是追求紀錄、呈現被攝者的真實肉身、生命與靈魂。
虛擬的世界裡,我們得以揣想、窺見人性的本質;真實的世界裡,我們直接闖入了被攝者的生活悲喜,因而得以發現或尋想生命的意義。
劇情片只能擬真,要求演員進入角色的軀殼和靈魂,要以專業的做作追求虛擬的夢幻;紀錄片則是試圖將真實人物、場景與事件帶到觀眾面前。關鍵在於,面對攝影機的時候,專業的人或者非專業的人還能有幾分真實,又帶有幾分做作?
專業人往往帶著意識與刻意的做作去忘我入神;
非專業的人則是帶著警覺和僵硬,刻意地去還原自己的本色。
專業的人掏洗得越乾淨,刻意得越不著痕跡,就越容易獲得好評;
非專業的人,拿掉更多的緊張和謹慎,才能找回原來的自己。
紀錄片的工作者為了超越攝影機的障礙,有的是直接把導演或採訪者都拍了進去,用自己的生命見証呼應影片的主題,拍攝者也成了被攝者;有的就是直接讓被攝者再次演出一次曾經發生過的故事;有的則是刻意迴避開攝影機存不存在的話題,剪掉所有的穿幫不自然,用人工修剪出接近客觀真實的作品……
形式上的刻意,表面上是要追求客觀的再現,或者是做出更有效果的誘發,其實,卻往往墜入更大的瓶頸魔障中。
因為,只要有攝影機在場,人就一定變得不自然。就如同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文章中所說的:「攝影是某種殺戮、掠奪,攝影是現代世界與現實、歷史、時間的掙扎。」好萊塢電影《偷情》中對於藝術創作的本質有過一次精彩辯論:以他們的故事來劃作可能是「強佔(taken)」行為,卻也可能是「借用(borrow)」
不管是強佔或借用,劇情片的演員刻意忽視攝影機的存在,「假裝」成為他的藝術成就關鍵;紀錄片的被攝者則是明確知覺感應攝影機的存在,能否繼續「率真」成為電影成就關鍵所在。只有攝影機不再是陌生人,攝影機是貼心的老朋友,紀錄片才有了呼吸和生命。
我不確知顏蘭權和莊益增花了多少時間和《無米樂》中的崑濱伯、崑濱嬸、煌明伯和文林伯這些老農夫相處,電影介紹中說他們前後拍了十五個月,拍出了三百五十小時的帶子,這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宿命,用生命拚命地拍,最後只能精剪出兩個小時的精華。
但是電影會說話,鏡頭讓我們看見他們並沒有站在田埂上,「客觀」地取樣拍攝農民的生活,電影中,他們只有偶而出現了聲音,沒有用鏡頭帶出自己把腳踩進稻田的泥巴裡,用最接近水田的蹲姿,流下和老農一樣辛酸的汗水才取鏡完成的影片;
他們不像一般新聞記者那樣喳呼式地走馬看花地採樣取鏡,更不像做研究的學者一樣刻意保持著距離,他們在農村裡一待就是十五個月,那十五個的停留與駐足,有如播種、耕耘、收割,才有《無米樂》的豐收,只有停留,才有思考;只有生活,才可能生根,才有生氣,才有呼吸……
後來,我才知道莊益增家住屏東,當兵退伍後回到屏東老家跟著蕉農老爸種了兩年的香蕉,後來才被我老爸趕出門,因為莊爸爸認為WTO帶來的農業革命,在台灣當農夫是沒前途的,但是莊益增學了拍片技術,還是回到他最熟悉的農田裡為台灣農民塑像也立傳。
或許正因為他們說著共同的語言,對台灣的土地有著相近的情感,從立夏的節氣開始訴說四時農家生活的時候,鏡頭穿透了所有人文和機械的障礙,一切就好像你赤腳踩進了稻田,一切就像陳明章的吉他音樂一樣,自然散發著濃濃的土香,汗從額頭流下,入口卻是鹹澀中帶有清甜。
《無米樂》最大的成就在於自然和工整。自然是天意,工整是技術,兩者兼融,就是藝術中的化境了。
先談自然。《無米樂》中的崑濱伯、崑濱嬸、煌明伯等人,明明白白知道身旁眼前就有攝影機在拍他們,然而表現得一點不生份、不僵硬,粗口和汗水就自然從他們的軀殼中流露了出來。
從每天早晨的三炷香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到下田犁地的高低不平,幹活時就把汗衫半捲,露出大半個肥肚囊,好壞拙巧都好,人生不必重來,不必偽裝;除起雜草,想起放牛的好時光,想起不願施藥傷地的不捨,喃喃自語的生命對白才是真性情,從他們的真情語言裡你就能明白「日出而做,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詩句,是何等率真有力地描繪著他們的心胸和志節。
他們是平凡的小人物,務農辛苦,隨口說出:「工作這麼多,錢卻沒有這麼多,錢如果像泥巴這樣翻來翻去不知有多好?」卻直率得讓人心酸;再聽崑濱伯說:「有時候晚上來灌溉,風清月朗,青翠的稻子映著月光,很漂亮!心情好,就哼起歌來,雖然心情(擔憂),不知道颱風會不會來,或病蟲害,也是無米樂,隨興唱歌,心情放輕鬆,不要想太多,這叫做無米樂啦!」
你卻只能跟著輕聲歎息,農人的辛苦,不是我們都市裡的文人,不是網路上咬文嚼字的人可以理解的,台灣老農對這塊土地的愛,就是《無米樂》最真誠感人的地方所在。
但是《無米樂》更大的成就不只是台灣老農真性情的躍然銀幕,精雕細琢的藝術成就,更是《無米樂》超越時下紀錄片的成就格局的關鍵所在。
顏蘭權和莊益增在那十五個月的工作期裡,其實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去守候和看景,每一個鏡位,其實都是絕美的構圖,都是從生命裡走過的汗水印像,都是打心眼裡,打生活裡對台灣農村之美最衷心的禮讚與歌頌。所以我們才會在明明最手工最純樸的農家生活中,看到最唯美,明明是雕琢,卻渾然不似工匠而是天意的畫面經營,成就最精彩的影音對話。讓紀錄片有好看的畫面,有動人的結構,有生猛的生命,才能結構出讓人驚歎的佳作。
時序已經又是炎熱夏季了,嘉南平原炙熱的陽光依舊讓人熱得發昏,但是台灣的稻田多數都要休耕了,農民佝僂的身影快要成為史書上的黑白的影紀錄了,台灣的農田未來會是何等面貌?沒有人知道,但是一部《無米樂》,為即將消失的影像留下最後的紀錄。
那是台灣的資產,那是台灣的寶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