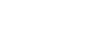發信人: bordergogo.bbs@bbs.wretch.cc (拒看蘋果日報!), 看板: movie
標 題: 【敗者之言─無米樂】
發信站: 無名小站 (Sat May 21 23:44:05 2005)
在城市裡住久了,我都快忘了兒時門口埕曬榖的香味。
小時候,我們一群小鬼,最喜歡在阿嬤耙穀的時候,在一行一行的稻穀小丘上跳著,邊玩著土地公或者紅綠燈。之後,我記起曾經母親嘴角黏著一粒米粒,盛滿一碗初碾的新米,再夾一塊滷透的三層肉鋪在上頭,她笑著說:「這新米盡好吃,趕緊撥飯。」
我記得父親把一袋袋米送去碾米廠,糶米換錢,他點著十來張鈔票,邊抽著菸,一邊喃喃自語,然後轉頭望望那十來包稻穀,走向我拿著四張千元大鈔給我說:「英文的補習錢,明天拿去補習班」
在向晚的風裡,我凝視著那一大片翻飛的稻海,小土地公廟的燈火悄悄亮了。我不知道我阿嬤清晨的祈禱會不會像康橋的炊煙一般,緩緩翳入天聽?只記得她在黃昏裡唱著不知名的日本歌曲,乾枯稻草燃燒著夕陽的晚霞裡,星子一顆顆探出頭來。
那都是我人生中絕美的風景畫。台灣破敗逐漸死去的農村,在工廠退休被苛扣退休金的父親、當他退休前夕一個人站立在公司強要他耕種的數甲地中的身影,仿佛在那一刻,他就永遠成為田裡的稻草人一般,木訥而寡言。
崑濱伯和煌明伯就像是我小時候,村子裡隨處可見的阿伯一樣親切,崑濱姆和崑濱伯之間的對話妙語如珠,那些我們這些老師一天到晚在學校訓斥學生不能講的「髒話」,在他們的口中竟是這麼自然近人。
他們的之間的愛情,很多時候都是從一些細微的小動作中呈現出來的,而沒有太多的濫情語言,崑濱姆似乎比較悲觀些,但是崑濱伯總是適時地開玩笑來化解她的鬱悶,或者就是這樣的互動,他們的愛情歷久彌新。
鏡頭開始,就是崑濱伯對著神明的誦禱,敬天畏神,正是農業社會的傳統,農民跟大自然之間的種種關係,或是收成遭到天災摧殘,或者是穀賤傷農的人禍,農民總是將自身的災厄歸諸於信仰的層次,甚至崑濱伯眼睛的殘疾,他甚至把它認定為是自己從前賣花生不夠乾燥而得來的業報。
煌明伯感嘆著他們是最末代的農民,他說從前他父親那一代四五十歲就可以「照日」(享清福),但是他做事到現在69歲了,卻只能準備做到最後一口氣死了為止。當崑濱伯趕在夜裡收割稻子,卻在碾米廠發現稻子的品質不好,硬生生少了 1500元的時候,當他自己回到家裡吃著冷飯的時候,他卻還是強作笑容,這時,無米真的樂嗎?不禁成為我內心無回應卻是掛在心頭的詰問。
當崑濱伯和崑濱姆在夜裡燃燒著稻草,「末代稻農」那張紅色的紙,好像也燃著飄飛在無言的夜空之中了,遍地的WTO火燄,吞噬了所有枯黃老去的稻桿了。
「末代滅農」,終於在台灣戰後將近五十年的農民被剝削史中,準備劃下一個句點。
我想起吳音寧去探望楊儒門時的感嘆:「我沒有辦法不感到氣憤。看春天的雨落在楊逵耕耘過、而今水田大面積休耕、農人哀嘆連連卻不忍責備政府的土地上;落在族群人數比黑面琵鷺還要少、原本是邵族種作狩獵的家園,民進黨政府說要拆了蓋飯店;落在台灣醫療史中唯一的痳瘋病院,樂生療養院,老人們坐在輪椅上看著雨絲,看著群山大樹,看著卑微一輩子的安居處所,可能面臨被挖被砍被夷成平地,蓋捷運。」
如果我們注定要面對著一個破敗而逐漸死去的農村;如果我們總是在面對一個不管哪一黨都為資本家喉舌的政治現狀;如果土地的愛可以只放在嘴巴上而不用動手做。
崑濱伯和煌明伯他們在田地當中的身影與巡田,不就是最後的輓歌,無言的招魂儀式?當左派勢力只能在台灣過往的歷史中被追悼,當左派勢力被統派勢力綁架,當左派勢力只能龜縮在學院當中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許楊儒門的炸彈就是一場向那即將死滅的農村最後的吶喊,血淋淋的敗者之言。
我出了台南的國賓影城,回家的路上去吃一家素食,我吃著素肉飯,總覺得那米是這麼的香甜,我好久沒這麼用心吃米了,腦中盡是崑濱伯和煌明伯的身影,我心裡響起一首陳昇的歌,那旋律如午后翻飛的稻海。叫做「農夫」。茲抄 錄歌詞於後。
農夫 作詞:陳昇 / 作曲:陳昇
你站在門沿 看著孩子的背影
讓手上的煙 在輕輕的顫抖
由於你的沉默 沒有閃亮的語言
就不想像有愛 跟你有些關聯
你在天明時出走 從來不問為什麼
有天你在回家的路上跌倒 才發覺已老
你坐在屋沿 望著藍色的天空
在手上的煙 已燃到盡頭
我以為我懂 懂得魚游在水中
而蝴蝶會哭嗎?答案飄在風中
你是否想過 生命的美是什麼
是兒女的笑容 還是心中那片田
你用生命來寫歌 歌裡沒有佔有
你若從不肯說出口 詩人顯得笨拙
這樣沉默的臉孔 心裡藏著什麼
你若從不肯說出口 詩歌就不豐富
你用生命寫歌 怎能沒有點疑惑
你若從不肯說 就讓答案留在風中
也許 答案就在~就在~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