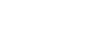作者: HW.bbs@hls.twbbs.org (找一個無聲的所在), 看板: movie
標題: 《聯合副刊》孤獨的四重奏
時間: 恨情歌工作坊 (Thu Oct 26 11:41:52 2000)
2000年10月26日 作者:劉若英 整理:王明霞
一九九九年夏天的末了,我剛結束《人間四月天》的後置錄音,整個人的情緒還延續著那齣戲,在錄音室裡看到自己演的張幼儀,心裡有點小小後悔,覺得自己進入那個角色太多,可能稍微主觀了一點——或許這就是演員的遺憾吧,總是在完成的作品中尋求更多更好的可能性。
秋天開始的時候我向自己正式宣佈——離開上一個故事!我把所有的沉重打包收進行李底層,決定讓自己像北京城蕭瑟秋日裡飄下的第一片落葉般輕盈,以一種全新的節奏邁向《夜奔》。
這種「落葉般輕盈的感傷」是我為《夜奔》所預備的情緒,因此我顛覆掉自己以往「埋」進劇本的習慣,選擇了用故事裡英兒靈動的步調呼吸、思考、生活,而不是企圖進入什麼狀態。
整體而言,演出《夜奔》對我是個特殊的經歷。面對黃磊、尹昭德及戴立忍三個戲劇學院表演系專業背景出身的演員,沒有受過學院洗禮的我有時不免相形渺小;但是聽他們討論表演方法或演員技巧之類的話題時,沮喪中還是會透出一絲興奮,因為我學到了如何從不同的角度觀察演員的特質。
黃磊是個聰明的演員,他能夠感應到對手的情緒並給予適當回應,讓人覺得窩心。私底下的他會用心跟對手建立關係,比如他和昭德非常會醞釀獨處的氣氛,培養兩人微妙的情緒,再把那種情感移植到演出中,並且和戴立忍之間適當保持一種戲裡的淡漠與疏離。我和黃磊因為已經很熟了,一個眼神就知道對方能到什麼程度,戲外反而維持著少東和英兒心靈交流的對應,不曾刻意建立什麼關係。
記得一場戲我把林沖的崑笛交給黃磊飾演的少東,當他把笛子從我手中拿走之後這個鏡頭就卡了,然後黃磊望著我笑了。那一瞬間我們心裡想的是同一件事——當他把笛子從我手中拿走時,我並不是那麼輕鬆把一個東西交出去而已。
我的手空著懸在那裡,因為覺得自己心裡的林沖被拿走了,就這樣愣著一顆心空蕩蕩的。現場沒有人看得出我當時內心細微的動盪,但黃磊就是能夠了解英兒當下的失落與悵然,因為他整個人的節奏和試戲時是全然不同的,那讓同為演員的我有種知音的感覺。
尹昭德是個不會放棄的演員,他可以日復一日練著別人看來枯燥無味的崑曲身段及唱腔,只為了讓自己更熟練劇中林沖的舉止和心境,他不在乎別人看來已經是極限的事情,反而付出更大量的努力讓自己不停前進。他的細膩內斂之於林沖很剛好,也很能激發出周遭人的動力,面對林沖那個深邃迷離的心靈,其他三人只能在氤氳中墜落。
看戴立忍演戲又是另一種感受,你會覺得那是種華麗而精彩的藝術,也有他屬於獅子座的王者之風。比如一個遞名片的動作,當他手一伸語氣一轉,你就是無法把視線從他凝練的神采上移開。我其實不太習慣看別人設計什麼,但是當他把設計變成一種不著痕跡的角色性格時,那就是成功的。
不管跟黃磊或是尹昭德、戴立忍演戲,都是過癮的事,你知道自己丟出的東西他們都有接到,也會回應,你就會被感動。我常想一部影片好不好看,就在於它是否比別人多了一點用心,就是那一點點的用心在打動人。
我喜歡《夜奔》因為它是個尊重觀眾的故事,是為了貼近人心裡最深處的感動而出發;裡頭的四個人其實都很孤獨,他們都只是個魂,身體與靈魂是疏離而斷裂的!
比如英兒雖然在現實裡過生活,她的魂卻一直留在戲台子上跟不同戲碼裡的角色作朋友;黃磊的角色也是,他的身體在紐約生活二十幾年,魂卻留在中國未曾離開;林沖更是如此,身為戲子的他在別人眼裡永遠只有演出的身分,沒有自己。黃子雷的孤獨感就更不用多說,他必須不停催眠自己得到了什麼,而實際上他只得到軀殼卻沒有得到心,那是一種生命的悲涼。
這個故事從大提琴的弓擦在弦上的第一句開始,然後是英兒和少東的對話,我常想如果沒有林沖出現,接下來他們會如何?成為一對理所當然繼續對話的普通夫妻?我不這麼認為。他們內心有其獨特深沉的纖細面——英兒會在空空蕩蕩的戲園子裡去跟那些戲魂交會,有些人可能在那裡掃了一輩子的地也不會這樣想,英兒卻是這樣一個人。
我很喜歡英兒對少東說的一段話——我寧願我們寫一輩子的信,我寧願熟悉你每一寸心,也不要你把心埋起來作我「理所當然」的丈夫!——因為是對少東,因為對象是林沖,所以英兒後來會做這樣的決定,那是一種 understanding!很難解釋這個字,那不單單只是了解或理解,而是真的能夠感同身受那份愛的感覺。
至於英兒對林沖——或許最初英兒愛的是戲台上的林沖,而非戲台下的真實林沖(比如現在許多人把「張幼儀」與「劉若英」劃上等號一樣);然而經過歲月歷練,當英兒脫去了年少時的青澀外衣,她對林沖的情感也相對從昔日的蒙昧中昇華,擴大到愛的全面了。經過林沖的生命,英兒這個角色展現了她成長的跡象。
感覺上黃子雷這個角色似乎是不受歡迎的,但他的存在卻正好反映出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你不可能只面對自己喜歡的,逃避那些不願接受的——用黃子雷來對應其他三人,也是這個劇本成功的地方。
透過這個角色我於是了解,世上所有事情都被衡量,唯有愛不能。因為黃子雷愛得純粹,以至於旁人無法再加諸責備;假設我們成為他,不見得能比他高尚。當一個人真能夠了解愛情的時候,就不會再去批判別人的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最打動我的,是那種大環境加諸於人的無奈——我們永遠都活在大環境之下,而不是單單活在兩個人的世界裡,妳喜歡我我喜歡妳就夠了。比如電影裡的那個時代,大家能不能夠接受少東與林沖這種型式的情感?或是那時如果沒有日軍侵襲,這個故事該怎麼說下去?同樣的情感,在不同的年代就會面臨不同的狀況與考驗,無可推諉。
現實的生活其實很像電影鏡頭,一幕幕的片段馬不停蹄翻轉過去,過去的一切無所謂原諒不原諒。
像英兒,她只是努力把自己料理得很好,讓感情不要被生活削弱。她會提醒自己勇敢去面對內心曾經被感動的部分,她會徘徊在戲園子裡尋找過往的身影,因為她要自己有感覺。或者也是這份提醒驅使著我們進入電影院,像英兒徘徊在戲台上追尋的腳步一樣,尋求各種被感動的可能性,因為心裡還存有生命最初的纖細感知沒被現實磨平。
有些人過了某個年紀或經歷一些事之後,就像翻過生命的分水嶺;銳利不再,只有被磨平的心靈和妥協的理想,他不覺得一場電影的感動是必需的——這很像少東,他努力要讓自己被磨平不想再敏感,因為怕了所以把自己封閉起來,因為他只要想到過去就是痛苦,直到英兒再度出現……。
有些生命裡錯過的遺憾和孤寂,在年輕時是無法被了解的,它像是胸口一塊永恆烙下的紅字 A,也像是心上的印記不能被攤開,只能貼身收藏。
故事裡的四個人像四種不同的樂器,用各自的特殊音色緩緩演奏,撫慰那些飄蕩在愛情荒原裡流離失所的寂寂靈魂。悠長無眠的夜裡只要你輕聲招喚,便會聽見耳際淡淡逸入那首,名叫「孤獨」的四重奏。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lovechang 的 bbs 電影板精華區
Copyright © 昔影.惜文. Template created by Volverene from Templates Block | Blogger Templates | Best Credit Card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
manhattan lasik and websites for accountants
Wordpress theme by Empire Themes